不是我的错:何时、由于何种原因,偏见归因能够保护自尊
Brenda Major
Cheryl R. Kaiser
Shannon K. McCoy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译者按:本文原题为“It’s Not My Fault: When and Why Attributions to Prejudice Protect Self-Esteem”,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三位学者。该文发表于2003年6月号的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杂志上,截至翻译日,Google Scholar上显示的引用次数是103次。原文请见http://www.psych.ucsb.edu/~major/lab/Major_Kaiser_McCoy2003PSPB.pdf
摘要:本文检验了这样一种假说,即当人们在面对负面结果的时候,对成为被歧视对象的可能性的感知,可以让个人获得一种对自尊心的保护。被拒绝参加某一课程的原因可能被受试者认为是性别主义,也可能是受试者的要求的正当性(deservingness),还有可能是其他纯粹的外界因素。无论何种性别,如果受试者认为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是性别主义,他们的自责程度就比较轻,会更少地把被拒绝归因于内在原因,而且期望这一类受试者比认为是由于自己的问题而被拒绝的受试者遭受更轻的抑郁。另外,如果把被拒绝一事归因于歧视而非自身原因的受试人数越多,就期望他们会经历更少的抑郁情绪。这些结果推进了我们对于何时、由于何种原因偏见归因能够保护良好情绪状态的理解。
关键词:归因;歧视;偏见;自尊;污名(stigma)
认为自己是某种偏见的对象——譬如由于性别、种族、性取向、或是外貌而导致的偏见——有着怎样的心理后果?当然,现在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表明,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与幸福(well-being)程度的降低是有着密切联系的(Major, Quinton and McCoy, 2002进行了评述)。另外,相关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自认为是某种普遍的歧视的对象的人,幸福程度也比那些不这样认为的人要弱。例如,自认为是被歧视对象,对女性(Kobrynowicz and Branscombe, 1997)和男同性恋者(Diaz, Ayala, Bein, Henne and Marin, 2001)来说,与抑郁程度正相关;对女性(Schmitt, Branscombe, Kobrynowicz and Owen, 2002)和非裔美国人(Branscombe, Schmitt and Harvey, 1999)来说,与低自尊程度正相关。(关于对偏见的感受对情感影响的来源,请参阅Kaiser, Major and McCoy待版书稿、McCoy et al., 2002、McCoy and Major待版书稿中的讨论。)
Crocker and Major (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假设,即,当污名(stigmized)群体遭遇到负面结果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有被当做是歧视对象的可能性同样也给予了他们一种保护自尊的方法(另见Dion, 1975、Dion and Earn, 1975)。依据Kelly (1973)的折扣(discounting)理论,他们假说,如果可以把偏见当做是一种说得过去的造成负面结果的外部原因,污名群体就会给他们自身在造成负面结果的原因中所占的地位打个折扣。另外,Crocker and Major (1989)假说,由于偏见来自于自身以外,相对于将结果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整体性的原因,比如说缺乏能力(613页)”,将负面结果归因于偏见能够保护情感和自尊。他们的假说基于情感定位(emotion positing)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将负面事件归因于自身以外的原因能够保护情感以及自尊,而归因于需要自己负责的内部原因,例如自己的要求的正当性(deservingness),则会导致负面情感和低自尊(例如,Abramson, Seligman and Teasdale, 1978、Weiner, 1985)。
最近,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2002b)挑战了Crocker and Major将偏见归因描述为外部归因的观点。他们坚称,因为一个人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是自性(self)的一个方面,因此偏见归因包含有强烈的内部因素。另外,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2002b)也提出了对歧视归隐能够保护自尊这一假说的商榷。他们辩称,由于歧视归因威胁到了自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歧视归因实际上会增强,而非减弱污名群体的负面情感(affect)。最后,Schmitt and Branscombe宣称,相对于低社会地位人群而言,歧视归因对高社会地位人群的伤害更少;这是由于歧视对于二者来说意义是不同的,对后者要更为温和。
在对他们的假说的一个检验当中,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进行了两个实验:在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想象,有一名教授拒绝了他们旁听一个封闭式课程的请求。在一组条件下(全拒情景),被试者得知那名教授是个“怪人”,所有人的旁听的请求都没有获准。在第二组条件下,被试者得知,那名教授是“性别主义者”,不让任何一个被试者的同性旁听,却准许了10名性别不同于被试者的学生的请求(偏见的情景)。实验者评定了被试者对歧视、个人原因(内部原因)、教授的原因(外部原因)这几大因素在他们被拒绝一事中起到的作用大小。除此之外,在第二个研究中,被试者指明了他们可能遭受到的12种情感,如沮丧、由于、愤怒、惨痛(cruel)等的强弱程度。
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的论断相一致,偏见归因的确具有内部成分,相对全拒情景,在内团体(ingroup)被拒绝的情境中,在被试者在两个实验中均把更多原因归诸内部因素。然而,与Crock and Major (1989)的论断一致,在第一个实验中,被试者对外部因素的归因的程度在偏见情景和全拒情景中一样高。在第二个实验中,相对于每个人都被拒绝的情况,被试者在内团体被拒绝的情境下甚至更加关注外部因素。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实验2)同样发现,处在被描述为“偏见”的情境中的女性,比那些处在被描述为“全拒”情境中的女性,报告了更普遍的负面情感。因此,如果女性由于歧视被拒绝,就会比由于纯外部因素被拒绝报告出更强的负面情感。Schmitt and Branscombe并没有在男性中观察到这一现象。
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的研究证明了偏见归因同时包含内部和外部两种成分,对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另外,他们发现了,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把被拒绝归因于偏见,其感受就会比将被拒绝归因于纯外部因素(例如,教授是一个“怪人”)更差。然而,Schmitt and Btranscombe的研究未能对Crocker and Major的主要理论假设进行充分检验。合理的检验应当要求(一)对歧视致拒和要求正当性(例如,缺乏能力)所导致的拒绝所造成的情绪效果进行比较;(二)将歧视致拒所造成的对自尊相关情绪(例如,抑郁、忧郁)的冲击与对其他方向上的情绪(例如,愤怒、惨痛)的冲击分开检查。
Crocker and Major的折扣假说并不要求歧视归因是纯粹外部的。实际上,这一假说假定歧视归因比个人要求正当性的归因更为外部。结果,将被拒绝归因于歧视就应当比归因于内在的、未定的、整体性的因素,如缺乏能力等,痛苦程度应当更轻。这是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例如,Jones and Berglas, 1978)和借口行为(Schlenker, Pontari and Christopher, 2001)——这两种行为在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使自尊受到保护(Snyder and Higgins, 1988)——的基本依据。Schmitt and Bramscombe对歧视归因和外部归因的比较颇有趣味,却并没有对折扣价说作出检验。合适的检验要求对歧视归因与要求正当性归因所导致的情绪后果进行区分。
Crocker and Major(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的理论分析同样为关注愤怒、敌意一类的情绪。实际上,他们描述了歧视归因对于污名群体的自尊相关情绪——例如,自轻(worthlessness)、抑郁、伤心、羞耻等——的意义。他们预测,歧视归因能够保护自尊免于被拒绝或是失败的伤害;而他们并未预测,歧视归因能够保护污名群体免于愤怒、焦虑。确然,在他们最初对于自己的折扣价说的检验中,他们区分了不同的情感类型。Crocker, Voelkl, Testa and Major (1991,实验1) 给接受过性别主义者评价和非性别主义者评价的女性提供了12项情绪词汇。这12项情绪词汇从多种情感形容词量表(Multiple Affect Affective Check List, MAACL)(Zuckerman, Lubin, Vogel and Valerius, 1964)中的抑郁、焦虑、敌意分表中选取。被性别主义者负面评价的女性,显著地表现出比被非性别主义者负面评价的女性遭受了更少的抑郁情绪;但是,她们却并没有显著地因此遭受到更少的敌意或是焦虑情绪。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 采用了与Crocker et al.(1991,研究1)相同的12种情绪词汇,但却是在综合了全部12种词汇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结果的报告。在现在的研究中,我们进行了对歧视致拒相比于要求正当性致拒对于情绪的不同意义的检验,并在实验中中区分了抑郁类情绪(抑郁、自轻)、敌意(愤怒、疯狂)、焦虑(恐惧、担忧)。
抑郁等自我取向的情绪与敌意等其他取向的情绪的区分是特别重要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感受到不公正与愤怒的情绪反应是相关的(参见Miller, 2001的评述)。愤怒也是人们感受到成为被歧视对象后的常见情绪反应(Swim, Hyers, Cohen and Ferguson, 2001)。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把被拒绝归咎于歧视的人会与那些把被拒绝归咎于能力缺乏或是一个“怪人”的人同样生气,或是更加生气。一些有关偏见的研究指出了将自我取向的情感与其他取向的情感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例如,Devine, Monteith, Zuwerink and Elliot, 1991;Vorauer and Kumhyr, 2001)。举例来说,Vorauer and Kumhyr (2001)发现了,和偏见心理较重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相比于那些和偏见心理较轻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只会经受较严重的自尊相关的负面感觉,而不会经受更严重的其他取向的负面感觉。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偏见严重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被试并未发现他们是被歧视的对象。这一研究提示我们,当目标经历过偏见行为,却并未把这些行为归于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负面行为归咎于个人。总而言之,该实验的目标在于利用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相同的范式来对Crocker and Major (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的折扣价说作一充分检验。
区分内部事因与自责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在于通过考虑自我担责(responsibility)归因与他人担责(blame)归因的情绪影响,把Crocker and Major (1989)提出的自尊保护假说扩展到简单的内外部归因二分法之外。Major et al. (2002)近来提出,污名者面对恶劣对待时,为保护自尊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并非是“是自身以内还是以外的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而是“是你还是我需要为此结果负责”。
歧视归因的一个必要组成在于,承认自性的某一部分(人的污名或是群体身份)有可能是某一结果的引起者。确然,这一事实的辨明,使得Crocker and Major (1994)提炼出了他们的折扣理论,将对结果的社会身份归因与基于社会身份的偏见归因区分了开来。Crocker ana Major (1994)注意到,尽管把受到的对待归咎于社会身份是内部归因的一种,这一归因方式却并不一定蕴含对不公平或是道德失当的假定,而这样的假定却是蕴含在偏见归因之中的。污名群体的一些成员可能确实会发觉,他们受到的对待是由于其他人对于他们社会身份的反应,这些人却仍然可能把这样的对待认为是正当的。结果,他们可能就会把他们遭受的负面对待归责于偏见而非自身。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比方说,目标发现污名处于自己个人控制之下的情形。有一例对超重女性的研究显示了以上状况(Crocker, Cornwell and Major, 1993)。被知晓她们体重的男性拒绝成为搭档的超重女性将她们的被拒绝归因于自己的体重,并没有责怪男性的偏见。
尽管Crocker and Major (1994)发现,歧视归因包含了对他人道德失当的感知,归因者却并不去分辨事因(causality)、自我担责、他人担责归因这些概念。有些学者辩称,大多数受试者对这些名词不加区分(Tennen and Affleck, 1990)。另外一些人则辩称,这些概念应当从理论上加以分辨(Fincham and Shultz, 1981; Shaver, 1985; Weiner, 1995)。例如,根据Weiner (1995),认为某人应当对结果负责,并不等同于归责于此人。他变成,即便是不利事件的原因在于某个人身上,而且这一原因还是此人个人所能够控制的,如果存在能够减轻道德责任的缓和情形的话,此人仍然不一定进行自我担责归因。另外,Weiner提出了将“对责任的判断,而不是对事因位置(内部还是外部)的判断才是情绪的决定因素。有充足的实证研究支持Weiner的假说(参见Weiner, 1995的评述)。
我们相信,对责任的判断对何时偏见归因能够保护自尊这一问题答案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偏见归因能够把对负面事件的责任从自身移除,并转移到歧视上去的话,这种归因就应当是自我保护性的(参见Major et al., 2002; Major, Quinton and Schmader, 2003; McCoy and Major待版)。换句话说,当歧视归因能够让个人给自己在负面事件中所要负的责任打个折扣的时候,歧视归因就能够保护自尊。
折扣理论(Kelley, 1973)的基础是Heider (1958)的思想,即对行为的解释通常包括人的内部与外部事因之间的权衡。最近有理论指出,内部和外部的事因并不一定是负相关的(McClure, 1998)。常会发现,对内部事因给予更多重视的行为,对是否重视外部事因没有影响;反之亦然。这一分析的意味着,歧视归因和自责并不一定是负相关的。感受到有人对自己的群体有偏见并不妨碍人把负面结果归责于自己的问题,如缺乏努力。类似地,感受到自己难以胜任某一岗位,并不妨碍把自己被拒绝的原因归于别人的偏见。结果,无论是只进行歧视还是只进行自责性归因,都不能调和负面事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比较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情绪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个人把负面事件归咎于自己及归咎于歧视之间的相对成都,亦即折扣程度。
Major et al. (2003)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实验中的女性均收到了负面反馈,其原因分为明显的性别主义、可能的性别主义、明显不是性别主义三组。歧视归因与自尊心的关系在不同实验条件下表现不同:例如,在明显的性别主义条件下,这一关系是正相关的;而在无性别主义条件下,这一关系是负相关的。不过,在所有情境下,折扣均与自尊正相关。亦即,越是把负面反馈归因于歧视而非自身能力缺乏的女性,自尊程度就越高。因而,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假说,认为对负面事件进行折扣(即,更多地归责于偏见而非自己)的人越多,被试者的自尊程度就会越高。
概述
本研究采用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的范式,检验了Crocker and Major的折扣假说以及我们自己的自责折扣假说的关键理论假定。男性即女性被试阅读了一小段场景,场景中描绘一名教授拒绝了他们想要参加某一课程的要求。三分之一的被试读到的内容称教授是“性别主义者”,只把与被试者性别相同的人排除在课堂外。这一情景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的“偏见”情景相同。另有三分之一的被试读到的内容称教授是个“怪人”,把所有想要参加他的课程的人都拒绝了。这一条件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的“全拒”情景相同。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试读到内容称教授“认为他们很蠢”,在这一“独拒”的场景中,只拒绝了被试者一个人参加课程。被试随后被询问,他们把被拒绝的原因归于歧视、内部事因、外部事因的程度,以及这些事因各自要承担多少责任。我们同样评估了抑郁、敌意、焦虑这三种情绪,分开检查了不同拒绝情景对于这三种情绪类型的影响。
我们预测,相比独拒情景,在偏见情景中,自责的程度会更低(假设1)。我们同样也检验了Crocker and Major (1989)的假说,假说认为相比于独拒情景,偏见情景中,对内部事因的的归因程度将会更低,而对外部事因的归因程度将会更高(假设2、3)。我们预测,相比于独拒情景,在偏见情景中被试者将会报告较低的抑郁情绪(但并非较低的敌意或焦虑情绪)(假设4)。最后,我们检验了折扣行为将会调和抑郁情绪之影响这一假设(假设5)。
方法
被试
被试者包括43名女性大学生志愿者、42名男性大学生志愿者(年龄M=20.84岁)。大多数(75%)被试者是欧洲裔美国人,其他人则据报告分别属于亚裔美国人(7.5%)、拉美裔美国人(8.8%)、非裔美国人(2.5%),以及其他(6.3%)种族背景。男性和女性被试被随机指定阅读三中小场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2(被试性别)×3(拒绝场景)的受试者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
过程
被试者阅读了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所使用过的小场景之一,在这些场景中一名与被试者性别不同的教授拒绝让他们来听一项被试者所需要的课程。教授的拒绝之性质由一个朋友(一定与被试者同性别)对教授的描述来操纵。所有被试都被要求想象如下场景:
引用
设想现在时新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你需要你需要去加修一个你的专业要求的课程。你去教授的办公室里,礼貌地请求他让你加入课程。遗憾的是,教授拒绝了你,并说:“抱歉,我不能让你加课。”过了几天之后,你跟一名好友说起没被容加课的事。你的朋友,作为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说他/她对那名教授不让你加课一事毫不惊讶。他/她告诉你……
对三分之一的被试者(偏见情景),朋友说教授是“性别主义者”,在拒绝了被试者之后又允许了不同性别的一些人加了课。对于另外三分之一的被试,朋友说教授是个“如假包换的怪人”,不允许任何人加课(全拒情景)。这些操作均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的偏见、全拒情景相同。而对于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试(独拒情景),朋友说教授“认为被试者是笨蛋”,除了被试者之外的其他人都被容许加了课。
独立性度量(dependent measures)
被试者指明了他们预期中把被拒绝加课归责于自身的程度(“没被允许加课,要怪我自己”,“没被允许加课,是我的错”,α=.70)。然后,被试者指明了他们预期中被拒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因素引起的(“教授不让我加课,是因为和我自己有关的原因”,“教授不让我加课,是因为做请求的人是我”,α=.82)、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因素引起的(“教授不让我加课,是因为和他/她自己有关的因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教授的态度或是人格”,α=.86)。这些内在与外在项目,也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中所使用的相同。被试者同样也完成了一组针对歧视感受的两项目操作检验(manipulation check)(“教授的行为是由于性别歧视引起的”,“教授是性别主义者”,α=.97)。所有项目都进行了7级评分,起点是1(完全不),终点是7(极度地)。
被试者随后完成了一项28项目的心情度量。抑郁情绪由多种情感形容词量表中的四个抑郁分表组成:沮丧、心情舒畅(fine)(反向编码)、活跃(反向编码)、由于(这些项目与Crocker et al., 1991以及Schmitt and Branscombe , 2002a,实验2所采用的项目相同),并另外新增了12项情感项目,其共同点是与自尊程度有关:自轻、自豪(反向编码)、尴尬、仿若失败、对自己失望、对自己满意(反向相关)、被羞辱、耻辱、比别人低等、悲伤、抑郁、窘迫。这18个项目构成了对抑郁情绪的一个高度可靠的度量(α=.94)。敌意情绪的测度则由多种情感形容词量表敌意分表的四个项目构成:愤怒、合作(反向编码)、残忍、欣然(agreeable)(反向编码)(这些项目与Crocker et al.以及Scmitt and Branscombe所用的相同),同样也有四个新增项目:疯狂、鄙视、易怒、敌对。这些项目也构成了一个可靠的度量(α=.83)。焦虑情绪的测度由Crocker et al.即Schmitt and Branscombe所用的多种情感形容词量表焦虑分表的四个项目构成:恐惧、担忧、平静(反向编码)、有把握(反向编码)(α=.65)。
所有项目都进行了7级评分,起点是1(完全不),终点是7(极度地)。最后,被试者提供了自己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族,随后我们对他们参与实验表表达了谢意。
结果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变量均由2(被试性别)×3(拒绝情景:偏见、独拒、全拒)的方差分析(ANOVA)进行处理。所有的显著性均由Bonferroni后验检验得出。图1显示了不同拒绝情景下的的平均归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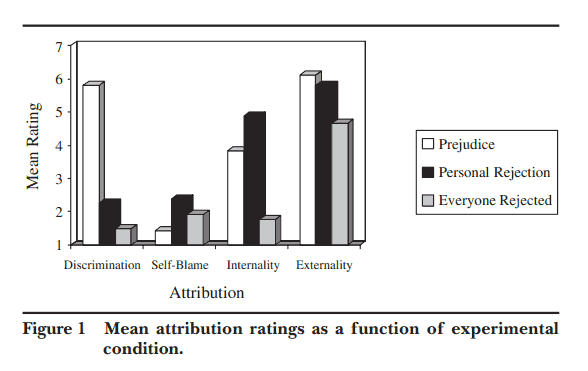
歧视归因
对歧视归因进行的操作检验获得了通过,F(2,79)=92.02,p<.001)。偏见情景中被试者对歧视致拒这一判断的评分(M=5.80, SD=1.26)显著高于独拒情景中的被试者(M=2.27,SD=1.66);而单据情境中的被试对歧视致拒这一判断的评分又显著地高于全拒情景中的被试者(M=1.48,SD=0.87)。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把被歧视归责于歧视(女性M=3.42,SD=2.12;男性M=2.90,SD=2.44;F(1,79)=3.97,p=.05)。交叉项不显著。
对被拒绝的归因
归责于自己。对自我归责的分析显著地表现除了拒绝情景的主效应,F(2,79)=5.72,p=.01与假设1一致,偏见情景中的被试设想中把教授的拒绝归责于自身的可能性与独拒情境中相比显著性较低(偏见情景M=1.32,SD=0.70;独拒情景M=12.39,SD=1.53)。而在全拒情景中,对自我归责的评分(M=1.91,SD=1.14)则落在偏见和独拒两种情景之间,而且与任一种情景的差异均不显著。被试者的性别在任何一组检验中均无显著效果,所有的F<0.55,P>.58。
内部事因。对内部因素评分的分析显著地表现出了拒绝情景的主效应,F(2,79)=31.17,P<.001。与假设2一直,被试者在偏见情景中(M=3.82,SD=2.06),相较于独拒情景中(M=4.89,SD=1.40),期望会更少地将被拒绝归因于内部事因。这两种情景之下,被试者均对内部事因的评分均显著的高于全拒情景下被试者的评分(M=1.76,SD=0.98)。没有包含被试者性别的主效应或交叉项存在,所有的F<2.25,P>.11。
外部事因。对外部事因评分的分析显著地表现出了拒绝情景的主效应,F(2,79)=11.37,P<.001。偏见(M=6.11,SD=0.88)及独拒(M=5.80,SD=1.13)情景的被试者均将教授对他们请求的拒绝归因于外部事因的程度均显著性高于全拒情景(M=4.66,SD=1.69)。尽管偏见情景中对外部事因的评分要高于独拒情景,与假设3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女性(M=5.86,SD=1.14)相较于男性(M=5.15,SD=1.59)更多地把被拒绝评价为外部事因所致,F(1,79)=7.22,p<.01。交叉项不显著。
情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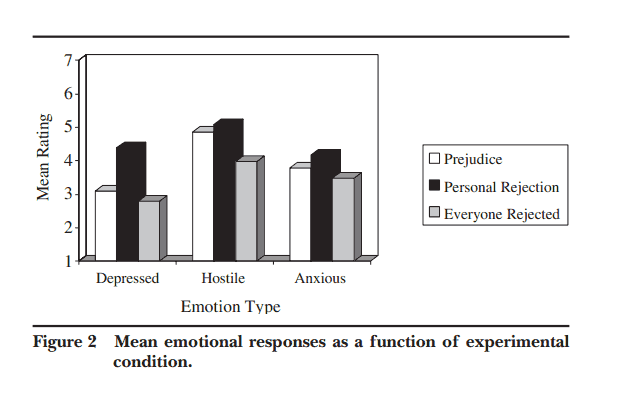
抑郁情绪。如同在图2中所显示的,拒绝情景对被试者的语气抑郁情绪水平有显著效应,F(2,79)=19.96,P<.001。与假设4一致,偏见情景中的被试者(M=3.10,SD=0.72)显著性地期望比独拒情景(M=4.40,SD=1.35)经受更轻的抑郁。而相较于全拒情景(M=2.80,SD=0..87),独拒情景中的被试者亦预期经受更严重的抑郁。偏见及全拒情景二者之间则未见显著差异。被试者性别的主效应,F(1,79)=2.07,p=.15,及其所包含在内的交叉项,F<1,均不显著。
敌意情绪。正如图2所显示的那样,对敌意情绪的分析显著地显示了拒绝情景的主效应,F(2,79)=11.87,p<.001。参观教育全拒情景(M=3.97,SD=0.96),偏见情景(M=4.86,SD=0.85)及独拒情景中的被试者(M=5.07,SD=1.00)设想中均比全拒情景中经历了更严重的敌意情绪。偏见和独拒情景二者之间则无显著差异。被试者性别未产生显著影响,所有F<2.22,p>.13。
焦虑情绪。拒绝情形显著地表现出了对于焦虑情绪的主效应,F(2,79)=3.10,p<.05(见图2)。在独拒情景中(M=4.17,SD=1.27),被试者预期要比全拒情景中(M=3.47,SD=1.02)感受到更严重的焦虑。偏见情景中的焦虑评分落在另外两种情景之间,与二者均无显著性差异(M=3.78,SD=0.85)。被试者性别未产生任何显著效应,所有F<1.64,p>.20。
调解(Mediational)分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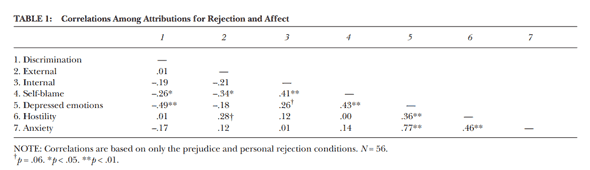
偏见与独拒两种情景中被试者的归因种类与期望情绪反应二元相关关系见表1。总体而言,歧视归因显著性与自我归责负相关(r=-.26,.05),并与对内部事因的归因负相关(r=-.19)(但这一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歧视归因与对外部事因的归因不相关(r=.01)。对内部和外部事因的归因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r=-.21)。另外,被试者越是不将其被拒绝归因于歧视(r=-.49,p<.01)、越是将此事归责于自己(r=.43,p<.01),他们就越是会报告抑郁情绪。对内部事因的归因与抑郁情绪正相关(r=.26,p=.06)。歧视归因、自我归责、内部归因与敌意情感和焦虑情感无关。
根据我们的折扣理论,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偏见的受害者,就能够通过将负面事件的责任从自身推到歧视上,使自尊受到保护。因而,我们认为,情绪反应的关键媒介是个人将负面事件归责于歧视相对于归责于自身的相对程度。我们并不期望,只靠歧视归因或是自我归责其中之一就能够调解(Mediate)实验条件与自尊相关的负面情感之间的关系。
为检验折扣假说,我们通过从被试对歧视的归因程度中减去被试的自我归责评分(这一技术亦见Major et al., 2003),构造了一个折扣变量。我们按照Baron and Kenny (1986)的步骤,随后检查了折扣是否调解了拒绝情景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我们检查了偏见和独拒对抑郁情绪之影响的调解程度,因为这些情景与折扣假说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的首个回归分析(见图3)检查了与哑变量0(独拒情景)和1(偏见情景)指征的实验条件是否能够显著预测抑郁情绪的程度。结果再现了前文汇报的ANOVA结果(β=-.52, p<.001; R^2=.28),F(1,54)=20.46, p<.001。我们的第二个回归分析检查了实验条件是否能够显著地预测折扣变量。与预期一致,实验条件与折扣程度是正相关的(β=.80, p<.001; R^2=.63),(F(1,54)=92.46, p<.001。应当注意,折扣程度与抑郁情绪是负相关的(r=-.57, p<.001),这意味着被试者越是把被拒绝的原因从自身推到歧视上,设想中就会感觉到更少的抑郁情绪。对调解程度检验的第三步则将实验情景和折扣同时纳入到预测抑郁情绪的回归中去。总体的同时回归是显著的,R^2=.30, F(2,53)=11.41, p<.001。这一分析显示出,折扣能够显著并且负面地预测抑郁情绪(β=-43, p<.03)。另外,当折扣程度纳入模型之后,实验情景与抑郁情绪的直接关系就不再显著了(β=-.19, p=.32)。对实验情景与抑郁情绪之间路径(path)之贝塔值(beta)的降低进行Sobel检验,结果是显著的(z=2.25, p<.03)。因而,与假设5一致,折扣调解了实验条件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
由于相对于独拒情景,在偏见情景下内部事因的评分同样显著降低,我们检查了相对于对歧视的折扣,对内部事因的折扣是否缓和了实验情景对于抑郁情绪之影响。我们构造了一个内部折扣变量(歧视评分减去内部事因评分),进行了与之前相同的一系列分析。实验情景与内部折扣是正相关的(β=.73, p<.001, R^2=.53)然而,在同时回归中,内部归因与抑郁情绪无关(β=-.25, p=.15),而实验情景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显著(β=-.35, p<.05)。因而,对内部事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