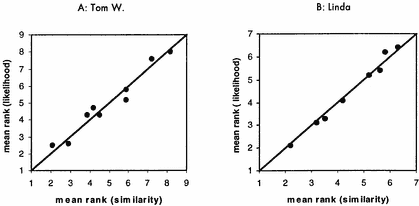两个大脑在运转,一个快一个慢
JIM HOLT 2012年07月25日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意思的是,卡纳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具体说来,他的贡献就在于他与另一位心理学家 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挑战、瓦解了经济学理论界长期抱持的一个概念: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性优先决策者。特维斯基于1996年逝世,享年59岁。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与其长期的合作者和挚友卡纳曼共享诺贝尔奖。
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挑战、瓦解了经济学理论界长期抱持的一个概念: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性优先决策者。特维斯基于1996年逝世,享年59岁。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与其长期的合作者和挚友卡纳曼共享诺贝尔奖。
“人类的非理性”是卡纳曼的主要研究对象。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和特维斯基做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实验,揭示了二十多个“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推理中无意识的差错歪曲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我们倾向于受正巧展露给我们的不相干数字的影响(例如,在一次实验中,经验丰富的德国法官如果掷出一对骰子后,刚好得到一个大数字,那么他们对商店扒手判的刑期就更长)。在第二阶段,卡纳曼和特维斯基证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定的人,并非如传统经济学模型所假定的那样行事,他们并没有“效用最大化”(maximize utility)。两人随后发展出另一种更符合人类心理的解释决策的理论,他们称之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卡纳曼便是因为这一成就获得诺贝尔奖)。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特维斯基过世以后——卡纳曼转向研究“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快乐行为学及其性质和成因。他在这一领域的发现证明是令人不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一个关键实验涉及一次故意延长的结肠镜检查。
《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内容贯穿了以上这三个阶段。这本书内容丰富,它清晰、深刻,充满智慧的惊喜和自助价值。全书读来妙趣横生,在很多时候也很感人,尤其是卡纳曼讲述他和特维斯基共事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获得的乐趣使我们变得格外地耐心;当你乐此不疲时,就不难做到精益求精。”)它对人类理性缺陷的洞见令人印象深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就宣称,卡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将会流芳百世”,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关键支点”。布鲁克斯说,他们“就像思想界的‘路易斯与克拉克远征’ ”。
间接宣布了人类的非理性
现在,该说说让我略微不安的部分。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关于过分自信。卡纳曼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专家,容易夸张地感觉自己是多么了解这个世界。当然,他自己对过分自信保持了警惕。尽管他和特维斯基(与其他研究者一道)宣称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现了种种认知偏差、谬论和错觉,他始终不愿勇敢地宣布,人根本就是非理性的。
抑或他做了间接的宣布?“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健康的,我们大部分判断和行动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恰当的”,卡纳曼在序言中写道。然而,就在几页之后,他又说,他和特维斯基所做的工作“挑战”了1970年代社会学家普遍持有的观念:“人大致是理性的。”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在正常人的思考中存在系统性的差错”:差错的出现不是源于情绪的恶劣影响,而是内置于我们逐渐演化的认知机制里。尽管卡纳曼仅仅提出一些最为寻常的政策建议(例如,合同应该用更清晰的语言表述),其他人却发挥得更多——也许是过于自信?比如,布鲁克斯认为,卡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工作表明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尤其是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扭转经济局面所干的蠢事。
这些过于笼统的结论,尚不论作者未必赞成,至少是令我皱眉的。而皱眉——你会在本书第152页了解到——会激发我们的怀疑:怀疑卡纳曼所谓的“第二系统”。实验表明,单是皱眉就可有效减轻过度自信;能让我们在思考中更善于分析,更加警觉;能让我们对那些因其轻易可得、条理井然而不假思索接受的故事产生疑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皱着眉头,持最怀疑的态度来阅读这本非常有趣的书。
在卡纳曼的模式中,第二系统是我们在思索世界时缓慢的、有意的、分析的、自觉努力的模式,第一系统与之相反,是我们快速的、自动的、直觉的、大半无意识的模式。在一个声音中听到敌意,或者毫不费劲地完成“面包和……”这个短语的是第一系统。而诸如不得不填写纳税申报单、把车停在一个很狭小的停车位等行为,则是第二系统在起作用(卡纳曼等人发现,有一个简单方法可以分辨一个人的第二系统在一项任务中所发挥的程度:只要盯着对方的眼睛,注意瞳孔的放大程度)
更宽泛地说,第一系统运用联想和隐喻快速、粗糙地勾画出现实世界的草图,第二系统进而达到明确的信念和理性的选择。第一系统提出意图,第二系统执行。所以,第二系统似乎是老板,对吧?在原则上是的。但第二系统不仅仅更有意图、更加理性,同时也是懒惰的。它容易疲倦(流行的术语是“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与放慢节奏、对事物进行分析相反,第二系统常常满足于第一系统提供给它的简单却不可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描述。“虽然第二系统相信自己乃行动之所在,”卡纳曼写道:“但自动的第一系统才是本书的主角。”当你心情愉快时,第二系统似乎尤其不活跃。
这时,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许会思忖,究竟要多认真地看待关于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说法。它们真是我们头脑中各自带有鲜明个性的一对小小的代理人吗?并非如此,卡纳曼说道,确切地说,它们是“有用的虚构”——有用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人类的思维习惯。
那个叫“琳达”的银行出纳
要明白这一点,请想想“琳达问题”(the Linda problem)。卡纳曼认为这是他和特维斯基一起做的“最著名和最具争议性的”实验。实验的参与者会听到一个虚构的、名叫琳达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单身,坦率,非常开朗,在学生时代非常关注各种歧视和社会正义。接着,参与者会接受提问,以下哪一个更有可能:(1)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2)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大多数人都选择了(2)。换言之,提供的背景讯息表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比“银行出纳员”更有可能。当然,这明显违背了概率法则(每一位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都是银行出纳;补充的细节越多,可能性就越低)。然而,甚至在斯坦福商业研究院受过大量概率训练的学生当中,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无法通过琳达问题。有一位学生在得知她犯了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后,答道:“我以为你只是在询问我的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简单的问题(叙述有多清晰连贯?)被一个更难的问题(它有多大可能?)替代了。在卡纳曼看来,这就是我们在思考过程中出现许多偏差的来源。第一系统匆匆得出一个基于“启发”的直觉结论——这是回答艰深问题的一个简单却不完美的办法——第二系统就懒惰地接受了这一启发式的答案,丝毫不想细查它是否合乎逻辑。
卡纳曼描述了许多这类经过实验证明的理性故障——“比率忽略”(base-rate neglect)、“有效性级联”(availability cascade)、“有效性的错觉”(the illusion of validity)等等。其结果就是逐渐让读者对人类的理性绝望。
我们真的如此无可救药吗?再想想琳达问题。甚至连伟大的生物进化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都受到它的困扰。作为一位概率专家,他知道正确的答案,但他写道,“有一个小人儿在我头脑里不断地跳上跳下,对我喊道——‘可她不仅仅是一个银行出纳;看一下描述吧。’”卡纳曼使我们相信,是古尔德的第一系统一直朝他喊着错误的答案。可是,也许发生着更为微妙的事情。我们的日常对话都发生在一个对期望未加说明的丰富背景下——语言学家称之为“言下之意”(implicatures)。这些言下之意可以渗透到心理实验中去。鉴于我们都期望让对话更加简洁,实验的参与者将“琳达是一位银行职”当作是在暗示“此外,她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是相当合理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答案就并非那么谬误。
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它却适用于卡纳曼和特维斯基,还有其他研究者所声称的在正规的实验中发现的一些偏差。在更加自然的情景中——当我们在侦查骗子而不是解决逻辑谜题,在推断事物而不是象征物,在评估原始数据而不是百分比的时候——人们就不太可能出现同样的差错。至少,后来的许多实验都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那么不理性。
当然,一些认知偏差甚至公然出现在最为自然的情景中。比如卡纳曼所说的“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我们倾向于高估利润和低估成本,因而愚蠢地施行一些存在很大风险的方案。例如,在2002年,美国人改建厨房,预期这项工作平均花费18,658美元,但他们最后却花费了38,769美元。
规划谬误“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乐观偏差的一个表现”,卡纳曼写道,这“很可能是最重大的认知偏差”。在某种意义上,一种倾向于乐观主义的偏差显然是糟糕的,因为它带来错误的信念——比如:是我们在掌控运气而不是运气在玩弄我们。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掌控的错觉”,我们在早上甚至都没办法起床吧?比起与之相对应的更立足于现实的人,乐观主义者更具心理弹性,具备更强大的免疫系统,平均寿命更长。此外,正如卡纳曼所指出的,过分的乐观主义使个人和组织都免受另一种偏差的麻痹效应,这种偏差就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我们对损失的畏惧更甚于对获利的重视。当约翰·梅纳尔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谈到驱策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时,他头脑中就存在着过分的乐观主义。
即便我们能够摆脱这本书所指出的那些偏差和错觉——卡纳曼以他自己在克服这些偏差和错觉方面殊少进步为例,怀疑我们也不能克服它们——我们也根本不清楚这是否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引发了一个根本问题:理性的意义何在?说到底,我们全都是达尔文学说里的幸存者。我们日常的推理能力为了有效地适应一个复杂的动态环境,已经随之进化了。因此,这些推理能力大概也会适应这一环境,即便它们在心理学家那些多少存在人为因素的实验中出错。如果理性的模范不是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推理的一种理想化,那它们又是从何而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判断存在普遍的偏差,就像我们不能在使用语言时普遍地不顾语法——抑或在对像卡纳曼和特维斯基所做的研究进行批评时也是如此。
幸福是什么?
卡纳曼从未从哲学上抓住理性的特征。然而,他为能够作为其目标的幸福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描述。幸福是什么意思?当卡纳曼在19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大部分对幸福的研究还依赖于询问人们在大体上对他们的生活感到多么满意。但这种回顾性的评估依赖于记忆,众所周知,记忆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此相反,一个人对快乐或者痛苦的实际体验能够随时随地取样,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加以总结,那会怎样?卡纳曼将之称为“体验的”幸福,与研究者依赖的“记忆的”幸福相对立。他发现这两种对幸福的衡量方式存在惊人的差异。使“体验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感到幸福的东西并不是使“记忆的自我”(remembering self)感到幸福的东西。尤其是,记忆的自我并不在乎持续时间——不在乎一段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经历持续多久。它会通过体验过程中痛苦或者快乐的峰值水平,通过体验的结果来回顾性地衡量一段体验。
记忆的幸福的两个缺陷——“对持续时间的忽略”(duration neglect)和“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在卡纳曼的一个更令人难受的实验中得到了惊人的展现。两组病人要接受痛苦的结肠镜检查。A组病人依照的是正常的程序。B组病人也一样,只不过——他们没被告知——在检查结束后,额外加上了几分钟的轻度不适。哪一组更痛苦呢?嗯,B组承受了A组的全部痛苦,然后还有额外的一些痛苦。但由于B组的结肠镜检查延长意味着结束时的痛苦要小于A组,这一组病人在回顾的时候就不那么在意(在更早的一篇研究论文中——虽然不在这本书里——卡纳曼提出,在这个实验中,如果B组受到的这阵额外的不适能够增强他们回来参加后续实验的意愿,它就是合乎伦理的!)。
在结肠镜检查中是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发号施令的是记忆的自我,而不是体验的自我。例如,卡纳曼引述研究表明,一个大学生决定是否重复一次春季假期,取决于前一个假期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而不是取决于那一个一个瞬间多么有趣(或者多么悲惨)。记忆的自我对无声的体验的自我施加了一种“暴虐”。“好像很奇怪,”卡纳曼写道,“我是我记忆的自我,而那个过着我的生活的体验的自我,对我而言就像一个陌生人。”
卡纳曼的结论听起来很激进,也许还不够激进。也许根本就没有体验的自我。例如,以色列魏慈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拉斐尔·马拉克(Rafael Malach)和同事进行的大脑扫描实验表明,当实验对象专注于一项体验,比如观看电影《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大脑中跟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部分不仅仅是安静了,实际上是被大脑的其他部分关闭(“抑制”)了。自我似乎消失了。那么,到底是谁在享受电影呢?为什么这种无我的快乐会进入记忆的自我的决策演算中呢?
显然,在享乐心理学中还有许多研究要做。但卡纳曼的观念革新已经为他在书中讲到的许多经验成果打下了基础:较之美国母亲,法国母亲与子女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但她们却更享受;穷人更受头痛的侵袭;独居的女人似乎与那些有配偶的女人享受着同等的幸福;在这个国家的高生活成本地区,一个收入大约75,000美元的家庭足够将幸福最大化。那些有志于降低社会不幸指数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在读到《思考,快与慢》结尾的时候,我充满狐疑的皱眉早已舒展开,脸上挂着智性满足的微笑。根据峰终定律来评价这本书,我会过分自信地催促每个人都去买来读。但对于那些只关心卡纳曼如何售卖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问题的人来说: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可预知的、快速反馈的环境中接受了10,000小时的训练——国际象棋、消防、麻醉学——那么,就不用看了。至于其他人,则好好想想吧。
吉姆·霍尔特(Jim Holt )的新书叫《世界为什么存在?》(“Why Does the World Exist?”)。
http://www.psychspace.com/space/viewnews-49125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11月25日。
翻译:流畅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