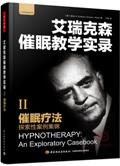前言
序
“没有不透风的墙”——索菲
每个了解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H.Erickon)的人都知道,他做每件事都有明确的目的性。事实上,他的目标导向性可能是他生活和工作最重要的个性特征。
为什么在与欧内斯特·罗西(EmestL.Rossi)共著《催眠实务》之前,他一直避免在书中展现他的工作呢?为什么他选择与欧内斯特·罗西合著?最后我禁不住猜想,“为什么他要我来写序言?”
不管怎么说,艾瑞克森在长达15年间发表了将近150篇文章,却只有少得可怜的两本书,一本是1954年与库伯合著的《催眠中的时间扭曲》;另一本是1961年与医学博士赫什曼和牙科博士赛科特合著的《催眠术在内科和牙科实践中的应用》。很容易理解在他70多岁时,他很渴望留下一份遗产,一份最后的总结,一个最终他人可以真正了解他和(有可能)仿效他的机会。
作为合著者,罗西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他与很多精神病学的巨匠有交往—弗朗茨·亚历山大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荣格学派的受训分析师。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并且在过去的6年中,他把他主要的时间奉献给了辛勤地观察、记录和讨论艾瑞克森的工作。
再者,“为什么找我?”我也是一位受训分析师,但来自不同的组织团体—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凯恩·霍尼)。我是一个执业近30年的精神科医师。差不多15年的时间,我做了很多残疾患者的心理治疗工作。从我第一次听说当时住在密歇根州埃勒维兹的米尔顿·艾瑞克森算起,我与催眠的联系有超过35年的时间。
罗西和我两人都有着丰富而不同的临床和理论背景,我们两个人的主要工作都与催眠无关。因此,在弘扬发展某一催眠理论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既得利益。我们真诚地致力于展现艾瑞克森催眠的理论和理念这一目标,不仅针对催眠实践者,也针对不甚了解催眠的精神治疗医师和心理分析师群体。朝着这个目标,罗西为了我们其他人的利益,摆出一副很天真的学生姿态,代表其他人扮演角色。
玛格丽特·米德也把自己看成米尔顿·艾瑞克森的学生,她在他75岁生日时,在《美国临床催眠杂志》刊文“米尔顿·艾瑞克森的独创性”(Mead,M.TheOriginalityofMiltonErickson,AJCH,Vol.20,No.1,July1977,pp.4-5)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她解释说,自从她在1940年夏天第一次遇见艾瑞克森在通过陈述表达他的理念之后,她对他的独创性便有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肯定地说,米尔顿·艾瑞克森如果能想到新方法—而通常他都能,就绝不会用老方法解决问题。”但是,她感觉“他难以抑制的、强烈的独创性成为传播他所知道的许多东西的障碍”,并且“那些爱刨根问底的学生会因为他每个示范中非凡而又意想不到的才能而沉思其中,在试图模仿复杂的特异性反应和他正在阐释的基本原理之间感到迷失。”在《催眠实务》和这本书中,欧内斯特·罗西用一些大篇幅来阐述这些基本原理。他最为直接地通过从艾瑞克森的案例中组织和选取相关材料来做这件事。但更有助益的是,他鼓动艾瑞克森清晰地阐明这些原理。
那些像我这样仔细研读这本书的学生将会发现,迄今为止,作者在澄清艾瑞克森在催眠性质和催眠治疗理念、催眠诱导技巧、诱导治疗性变化以及验证这些变化的方法等方面已经做了最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披露了很多关于艾瑞克森生活和治疗理念的有益资料。许多治疗师,包括心理分析师和其他人,将会发现艾瑞克森的方式和他们自己的方法可以兼容并存,并与他们关于“催眠术”的先入之见相去甚远。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催眠不会改变一个人也不会改变过去的经验性生活。这有助于允许他对自己了解更多,并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治疗性催眠帮助人们绕过他们自身的习得性限制,让他们可以更完全地探索和利用其潜能。
那些阅读了艾瑞克森慷慨提供的吸引人的案例然后试图模仿他的人,肯定会发现他们无法取得可与他相提并论的成就。他们可能会放弃,并宣称艾瑞克森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可能会强调艾瑞克森患有好几种残疾使得他与其他人不一样,并且肯定会承认他有着独特的观察和回应方式。他天生患有色盲、听力障碍、阅读障碍,还缺乏节奏感。他遭受过两次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侵袭。他因为神经损伤,再加上关节炎和肌炎的影响,使他在轮椅上度过了很多年。然而,有些人不会满足于艾瑞克森是一个无法模仿的治疗学天才这种解释。他们将会发现在欧内斯特·罗西这样的澄清者和推动者的帮助下,艾瑞克森的工作方式有很多可以被他人学习、传授和利用。
在《催眠实务》中,艾瑞克森自己曾建议“针对困难问题进行工作,你可以在处理过程中,尝试进行有趣的设计。通过这种方式你会得到解决这种困难问题的答案。这会让你对构思设计感兴趣,而忽略令人辛苦的具体工作。”在处理分析和传授艾瑞克森式催眠这个困难问题的过程中,罗西的方案可能是最有帮助的。每个读者是否会选择接受罗西的建议,运用这本书里所推荐的这些练习,这完全是个人问题;从我的经验来看,练习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一个明显的结果是:通过慎重而有计划地运用一些罗西用下划线所强调的艾瑞克森方式,我发现我已经能够帮助患者体验更深的催眠状态,并且似乎更容易接受作为其结果的变化。我发现设置治疗性双重制约、给予间接后催眠暗示、通过询问助长治疗性反应,以及建立复合暗示是特别有用的。艾瑞克森和罗西再三强调他们所称的利用方式,无疑是事出有因的。在这本书里,他们举了很多生动实用的关于“接受和利用患者的显在反应、利用患者的内部现实、利用患者的阻抗、利用患者的消极情感和症状”的案例。艾瑞克森对笑话、双关、隐喻和象征的创造性使用,已被其他人分析过,尤其是哈雷、班德勒和格瑞德,但本书里的很多例子和讨论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的理解。
有时候,艾瑞克森会与患者在他称之为常见日常恍惚的浅催眠状态下工作,或完全不用催眠。他并不把自己局限在短期治疗中。这在他与彼得,一个嘴唇肿胀的笛子演奏者,为期9个月的艰苦工作中得到了说明,这在本书中,罗西以一种生动的案例梗概形式对其进行了描述。但是,他与处于最深催眠状态、往往带着治疗性遗忘的患者打交道时所呈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经常让观察者非常感兴趣。是诱导出深度催眠、给予指导还是间接而非直接的暗示、产生更彻底的还是更持久的临床效果,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已经成了我的经验: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或不珍视深度催眠,并且不曾为之尽力,那么他就不大可能经常看到它们。我的经验也表明,深度催眠状态的获得,经常包括像是解离、时间扭曲、遗忘、年龄退行等现象在内,它可以在患者的症状和态度上引起更快并且似乎更深刻的变化。
艾瑞克森强调帮助患者在我们所称的“无意识”模式中进行工作的价值。他重视无意识的智慧。事实上,他经常不遗余力地维护治疗性工作,以避免患者意识心理的审查,避免可能被患者的“习得性和限制性定势”破坏。他的这种做法在这本书中比在迄今为止其他任何已出版的作品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概括。
当然,他往往并不把催眠诱导或催眠性技术与治疗性技术或演练分得那么清楚。他觉得治疗师在催眠诱导中使用无意义的、重复的短语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可被更有效地用来注入治疗性暗示或让患者做好改变的准备。就像罗西曾经指出的,无论治疗还是催眠,包括诱导,在早期阶段,都包含一个“弱化患者平常受限的心理定势”的过程。艾瑞克森从来不是仅仅关心引起一种催眠,他总是更关心那些治疗性作用。
尽管他确实知道利用直接暗示、催眠性技术经常可以增强诸如系统脱敏和认知再训练等行为矫正方式的效果,但他还是指出直接暗示效果的有限性。他说:“直接暗示……并不会引起对实际的治愈所必需的意念、认知和记忆的重新联结和重组。催眠心理治疗中的实际效果……只能源自患者的活力。”于是,他引导并训练患者在决定为达成期望目标所需工作量方面的临床决断力(Erickson,1948)。从这个专辑,并从阅读本书以及其他出版物的案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相比于大多数治疗师而言,艾瑞克森较少需要及唤起“教条性的顺从”。
显而易见,“临床辨别力”不过是来自多年在动力学、症状学和康复保健方面的深入研究,来自与患者的实际工作。
治疗师的判断也会受到他自己人生观和生活目标的影响。艾瑞克森自己的人生观体现在他对“成长、喜悦和快乐”等概念的强调上。对这一点,他一再说,“生命不是什么你今天可以给它一个答案的东西。你应当享受这个等待的过程,这个你正在变得如其所是的过程。最令人欣喜的事莫过于种下一粒花籽,而不知道什么种类的花将会破土而出。”我自己关于此事的经验在1970年对他的拜访中得到了启示,当时我与他交谈了4小时,留下的感觉是我花费这个时间主要是在听关于他的家庭和患者的故事。直到1977年的夏天我才再次见到他。当时,早上5点在凤凰城的一个旅馆里,当我在回看艾瑞克森工作的一些录像带时,一些重要的顿悟逐渐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明显地与我们1970年对话期间开始的工作有关,也与中间七年我所做的自我分析有关。那天早上之后,当我兴奋地向艾瑞克森提及这些顿悟时,他只是报以他经典的微笑,而无意以任何方式对它们详加解释。
当我们在阅读诸如家庭疗法或完形疗法等一些其他疗法的著作时,我们会为他们如此多地受到艾瑞克森的影响而感到惊讶。决不偶然,这些学校里许多早期的治疗师曾从事催眠治疗工作,甚至与艾瑞克森本人一起工作过。我希望罗西在他将来的著作中,将会追踪其中的某些影响。在我的文章《对会心完形和催眠技术的新近体验》(Rosen,S.AmJ.Psychoanalysis,Vol.32,No.1,1972,pp.90-105)中,我提到过了其中的部分影响。
与艾瑞克森和罗西合著的第一本书《催眠实务》一起,《催眠疗法:探索性案例集锦》,为艾瑞克森式治疗或艾瑞克森式催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课程可能会辅以其他书籍,包括杰·哈雷以及班德勒和格瑞德所写的。另外,我们现在很幸运地有一个可资利用的目录,它由艾瑞克森亲自所写的147篇文章(见Gravitz,M.A.和Gravitz,R.F.,《美国临床催眠杂志》1977,20,84-94“完整目录1929-1977,”)组成。
罗西曾告诉我,在与艾瑞克森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常常受到艾瑞克森似乎是“非理论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打击。我注意到,这符合艾瑞克森的开放性,却肯定不符合他对成长的强调或他的人本主义的或社会取向的观点。罗西以及其他人时常重新认识艾瑞克森工作一贯所朝向的目标—那些患者的目标,而不是他自己的。今天这似乎不算是一个多么革命性的理念,这已经是几乎所有治疗师都公开承认的一个意旨,但或许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受到我们落实这个意旨的能力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意旨和实践两者在那些可能是世界级临床催眠大师的人的工作中,都得到了最为成功的协调和利用,可是,催眠术几乎在每个人眼中仍然与操纵和暗示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典型的艾瑞克森式悖论。
这个“操纵大师”容许并激发最大的自由!
西德尼·罗斯医学博士
纽约
201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