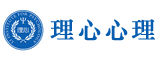近期在IAPSP的论坛中,官方推荐了 Sarah H. Pillsbury的论文《MUTUAL EMPATHY: IMAGINED SYMBOL AND REALIZ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供大家赏阅和讨论。这篇论文首次报告于2017年IAPSP 芝加哥年会,后刊登于《Psychoanalysis, Self and Context 》。
和劳拉,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一起工作,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她认为我不能像她之前的犹太人治疗师那样,能够理解她。
在治疗开始时,她很难理解她父母的创伤及其对她自己内心世界的影响。她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却一直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否认他们的情感和如影随形的死亡幽灵。但我能感受到她对连接的强烈需求。然而有一天,这种连接受到了挑战。当时,我戴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与一位我非常关心且关系很近的家庭成员有关。那个被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十字架,还是很偶然地被看见了。我们设法修通这种共情的破裂,并且,劳拉通过教我关于犹太教和大屠杀,开始逐渐信任我。当劳拉非常脆弱的,以胎儿的姿势躺在我的沙发上,光着腿同时发出尖叫的时候,一种深深的情感连接被建立起来了。我有些冒险地移动我的沙发,试图坐得离她更近些。然后她那悲伤的、骨瘦如柴的手抓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只我可以连接到她已经死在集中营里的外祖母的手。这个轻轻的手的相握,使她平静了下来,并且成为了治疗中的一个关键点,一个通向新的道路的转折点。后来,当我脆弱的某个瞬间,在那条路上,她能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共情走向一个完整的循环,在劳拉和我之间所产生的双向共情,完全对应到了那种我曾经渴望的,并强烈体验到的共情。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的分析师和我之间所体验到的。
关键词:想象符号 双向共情 创伤治疗
在和一位受过经典沙利文人际关系理论训练的分析师一周做4次分析的第7个年头,躺在他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里的沙发上,有一刻我开始注意到: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来,通过他的头顶,落在大金鱼缸前他那橄榄绿色的小长方形毯子上,一只大金鱼独自在鱼缸里游着。我的分析师Dr.S像往常一样,继续着他的针绣。提供着一种令人安慰且包容的存在。我不记得他说过了什么,也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这是太久之前的事了,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现在,我认为它们不重要了。但或许,也还是很重要的吧!但是它们的影响是巨大和直接的,给我留下了一个持续且深刻的印记。在视觉上,我开始觉知到一个不太符合常规的方形,好像这个方形以他的心为中心点,被拉变形了。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能清晰地看到那个形状。但那时,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分析师说起过。我认为我甚至不允许它完全到我的意识里面来,直到近期,我对科胡特(1984)《精神分析的疗愈之道》第九章开始重新阅读。慢慢地,这个形状在我的视觉意识里固定了下来,但是还是很久以后,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有关形状的概念。在我的第一次体验到强烈的情感之后,我花了随后几年的时间,去理解这个想象符号,就是后来我开始意识到的,我的分析师如此深刻地共情到了我童年的奋斗和痛苦。在那之前或从那以后,甚至包括在随后两段的分析里,我从没有体验过人类的这样性质和量级的共情。我现在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和Dr.S一起治疗的那些年里,我开始吸收和内化那个想象的符号,那个符号是我曾经直接在我分析师的身体上想象出来的。我后来的两段分析给我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需要和固执的渴望,就是那种Dr.S曾提供的共情,以及因我发展的需要而推动他产生出来的共情。我那时还不能认识到我是有多么需要另一个人的同频,另一个人像Dr.S那样陪伴我,在我独特的成长道路上。直到很多年以后,这另一个人又出现在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境里。
这个不规则变了形的方形已经被内化在我心里的某一处。但它又没有呈现出它原本的样子,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隐匿,直到最近才开始意识到,通过我的临床工作和教学以及写作过程,能够促使我进一步将它概念化和可以更清晰地表达。现在,我能看到那个向一侧倾斜的方形,一直在我的内心。我把它和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分析师的刺绣,以及那只独自游弋的大金鱼联系在了一起。我意识到我是如何内化了他的共情,并隐匿起来,直到我开始和劳拉一起工作时才被意识化,也就是下面我要报告的这个案例,和要开始写的这篇文章。
我有一种感觉:即使拥有Dr.S如此温暖的共情,我内心的一部分仍然是封闭的,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感知和体验的。也许你们有些人还记得,80年代后期艾滋病致命的传染,不幸的是,Dr.S也患上艾滋病并突然死亡。因此,我和他的工作也非常令人心痛地被地中断了。当他请假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没人知道,他在和艾滋病战斗。我甚至无法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他给予我的共情,取而代之的是我的迷茫和对他的多次缺席的愤怒。因为我不知道Dr.S病得那么重,所以我没能打开地给予向他更多的共情。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我的一段痛苦的回忆。
当双方可以相互接受并给予共情这样一个双向过程发生时,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认为这种共情就是双向共情。我的分析师Dr.S不让我知道他病的有多重,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羞耻感以及他所受过的经典分析的培训背景。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共情,然而,我却从没有机会去回报给Dr.S。然而在和劳拉一起艰难的分析过程中,以及在几次我私人的危机事件中,双向的且能被接收到的共情发生了。
共情,是科胡特在1984年给出的概念,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对科胡特来讲,分析师逐渐地进入到来访者的内心体验中,以分析师自己的心理体验为工具,提高对来访者的共情。然后,来访者通过内化分析师的共情,变得更有能力将一个有同理心的分析师带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提升她核心自我的共情理解能力。另外,正如Slavin 和Kriegman( 1998/20005)提到的:在整个治疗期间,在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这种共情过程的内化,是获得明显的改变和治疗结果的关键,或许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的是,其实分析师在其中也获得疗愈和生命的改变。
即使是单项共情,如果分析师没有找到来访需要的那个点,分析师的共情很可能就变得不足。在某一刻当科胡特(1984)对他的某一个病人不能同频的时候,当时他给出的解释并不是一个本真的共情:他的病人感觉到的是被二次伤害并且多次表示对分析师的不满。最终,科胡特意识到共情一定是来自分析师内心深处某一个非常真挚的位置。如果分析师的话语不能表达分析师本真的自我,这些话听起来就会觉得空洞。科胡特写道:“我不能充分感觉到他的感受,所以我给他的只是一些话语,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因此,我就重复做了那个来自他生命早期的非常基本的创伤。”科胡特继续写道:分析师只有持续的真诚地将病人的责备,作为一个(心理上的)事实来接受,经过一个冗长的(但最终会成功的)探索他自己内心的努力过程,并且去除他内心里的那个障碍,也就是在他对病人进行共情路上的那个障碍之后,最终才会有一个扭转(治疗的)局势的机会。
科胡特的坦白是如此诚实,这令我惊讶。正如科胡特所描述的,单向共情对治疗和对扭转治疗局势是必要的。为了让病人真正的相信这份共情,这共情就必须足够深入到分析师的自体要去感受那份对病人的真挚的本真。正如科胡特描述的这个过程是一直被重复的,现在,通过自体客体功能和与分析师之间的相关体验的逐渐增长,病人的核心自体已经明显被加强且稳定了。
然而,正如我看到的,双向共情要求分析师不仅要向自己的内在看,自己在表达对病人的共情上保持诚实,同时还要允许来访者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分析师。幸运的是,劳拉向我给予了她的共情,基于我本真地打开我自己。虽然那时候我不是故意而为的。但重要的是,当劳拉表达她的共情,她能感受到她的的共情能被我感受且被我认识到了,并且这个共情变成了治疗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orange,2010)。
和劳拉的一场渐进式交锋
在个人咨询的第一年,劳拉坚持认为,尽管她的第一个治疗师推荐她来我这里寻求夫妻治疗,但她还是不确定,是否我们的个人治疗是适合的。她说:“毕竟我的第一个治疗师是个有高智商的犹太男人。和他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舒服,虽然他有的时候非常强势和直接。举个例子,他坚持要我间隔3年再生第二个孩子,我完全服从了。你看起来不像他那么强势,这让我感觉到很不一样。你很少强迫我。在我大学最后一年里,我陷进大量的情感挣扎中,他却很有信心,并且帮助我度过了那个阶段。那时候,我的朋友很少,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大学生活。”
然后她又补充道:“现在我有了一个成功的婚姻,两个孩子,而且他们即将成年。并且我有了很多朋友。除了眼下我对儿子所受痛苦的焦虑,还有我自己有时无来由的恐惧和担心我年纪越来越大近90岁高龄的父母之外,我都还挺好的。”我感觉到劳拉并不是很确信她自己说的,然而她却坚持说她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她很害怕信任我,因为对她来讲,那可能会剧烈地动摇她的信念。可以肯定的是,她感到我们在宗教立场上的不同,这将我们严重的分裂开来。“很明显,因为你金发碧眼,所以你就很可能是一个新教徒或者基督徒(这是引用的她的原话,不是我的)。正如你知道的,我第一个治疗师是犹太人,所以毫无疑问,他能通过很多种犹太人独有的方式来理解到我。你怎么可能理解犹太教徒呢,犹太教安息日的圣餐,有关我信仰的那些传统,以及我犹太教(正统的)的精神世界?”她强调说:“而且,你怎么可能完全的理解大屠杀带给我们家庭的灾难性的影响呢?”有的时候她为了教我更多而向我解释:“Shoah这个词,也就是人们在欧洲所用的大屠杀这个词。”
有段时间,我的一个家人的健康方面出了点问题。这让我感到特别脆弱,于是我就在脖子上带一个小小的银色十字架项链。我故意把这个小十字架挂在脖子后面的钩子上,为了使它不被我的任何病人看见。但是有一次,它还是无意中跑到了脖子前面。在我的所有病人之中,只有劳拉注意到它了。她直接指着我的脖子问:那是个十字架吗?我认为,这对她来讲,就是她需要的那个可以用来证明我不能够理解她的证据。我们太不一样了。然而后来,她带着狡黠的笑容告诉我一件让她感觉解气的事,就是有一次当她常规地去找我推荐给她的那个犹太精神科医生时。她对那个医生说:“我来自己一个犹太德国家庭,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我却要和PILLSBURY医生一起工作。”她念我的名字时,加重了音调,似乎在暗中嘲讽我是个白人至上的新教徒,然后她自己窃笑起来。在我们下一次咨询之前,我摘下了我的小十字架,因为考虑到了她的不舒服,还有我的不舒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反复地向她强调:我真的没有宗教立场,我也不去教堂。我解释说,我只是临时带了那个十字架。“因为在那时,一个正在为她的健康而挣扎家人,引起了我强烈的担心。”我告诉劳拉,我非常尊重犹太教,尊重他的家庭在纳粹体制下做出的英雄般的英勇斗争。我再也没有戴那个十字架(幸运的是,我的那个家人从健康危机中活了下来。)
逐渐的,劳拉和我的咨询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是在一次咨询中,她心情激动地带来了几件他父母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文物”,其中她父母的一个带着纳粹徽标印章的护照,使我如此深切地感到一种不寒而栗。她还给我看了战后她母亲在巴黎拍摄的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她讲述了更多的细节,战争期间在法国,她的母亲不得不隐姓埋名。并且,更有意思的是,她,劳拉,能够通过她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本书,那本书记载了她母亲和其他年轻的犹太女孩躲藏在法国南部一个避难所的经历。由于劳拉的妈妈很少甚至好像从没有提到她战争时代的经历,劳拉只能通过她所知道的母亲过去在欧洲的一些事情,来自己拼凑那段经历。很显然,法国当地的修女故意把她妈妈伪装成一个地道的法国人。她只说法语,因为讲德语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就会被暴打。她妈妈用了一个法国的名和姓。那时她大约转为信仰基督教,并且为了将来在酒店工作,她在当地的厨师学校接受培训。
劳拉开始更多地向我敞开,在这段治疗期间,当她和我分享她的世界以及她父母的过去时,我很多次热泪盈眶。有一次,当眼泪轻柔的流到我面颊上的时候,我对劳拉说:“我想,我的眼泪是为你父母被迫忍受的苦难、暴行和悲惨的境地而流。”她看着我,可她的眼睛始终是干的。她说:“我感受不到那些故事,我哭不出来,我多希望我能。”虽然,在阳光照射进咨询室的那天,当我想象的那个模糊的正方形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和我的分析师之间连接,但是此刻我还是感觉到,劳拉正在感受着我如此深刻和深入共情,这是一种意识原型,它正在开始形成。
从这次开始,劳拉好像在对自己自言自语:“好吧,从现在开始,我将尽最大努力去接受你的不同,但是我需要通过教你更多的犹太教的知识、犹太人的习俗、犹太意第绪语及希伯来语的常用短语,和教你了解格里高利历法(公历)和希伯来历法的不同,来让你了解我更多。”作为开始,她带来了她心爱的近期手工缝制的披巾(犹太教男人晨祷时的披巾),向我解释它的用法,接着,她动情地朗读了一段希伯来的祷告,并且还给我留了一份。我们的咨询开始不时地呈现出更多的亲密感,当她开始更加放松的“教我”,成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咨询进入了高品质的阶段。
一只伸出去的手
劳拉就这样继续跟我做咨询治疗,做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治疗的第四年,有一次在咨询中,她变得极度的焦躁不安。起因是他儿子在新城市里,在他不喜欢一份新工作里进行自我调整时,所表现出的持续性无能。在那次咨询的前一天晚上,她的儿子深夜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向她倾诉他的焦虑和挫败。当她向我讲述这个电话的时候,她在愤怒中爆发了。她强调说她知道这都是她的错,她的来自父母的被内化了的创伤,现在通过她传递到了她儿子那里了,他注定会失败。她感觉到无望和无助,她开始激动地向上踢腿,并且大声叫喊着。
我坐在她身旁等待着,感受到我需要做些什么去缓解她的焦虑和她的破碎。为了能在可怕的痛苦中给到她帮助,我慢慢地试探性地从离她沙发有近5英尺远的地方,我经常坐着的保持着专业、安全距离而又舒服扶手椅中站起来,坐在她坐的沙发上,紧挨着她。我在早期自我心理学训练的自体和我当前的回应的同频的自体心理学的自体之间,心神不安地来回摆荡,这种不自在让我去全身心地感受我自己。这种即兴做出的新方法,对劳拉和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通常,在那两个方向之间,我感受到有一点难以选择,这个靠近相当冒险。我知道劳拉一直渴望能和她的母亲有物理上的靠近,但她的母亲是如此心事重重和内心受到创伤,以至于对她来讲,给女儿一些回应实在是太难了。当她的妈妈处于这样的痛苦中的时候,劳拉一直在努力地不让自己去感受到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当我走过去坐到沙发上她身旁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的权衡过我是否该这么做。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决定,是对劳拉悲痛的一种真实的回应。
坐在沙发上,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沙发柔软的天鹅绒般质地的纺织物,给我的感觉竟然是一种可怕的冷,一种被耗尽的、被遗弃的感觉,并不像我期待的和想要的那般温暖。劳拉躺在那里,把自己卷曲成一个自我保护的球形,她的一只瘦弱的、苍白的、骨瘦如柴的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这是一只我可以连接到她那死在死亡集中营里外祖母的手。此时此刻,我们被集中营的味道笼罩着。我感觉到死亡的存在,死亡就在这个房间里,和我们在一起。她的手让我感觉到无尽的悲伤,当我触碰到她时,准确的说是当我们的手轻轻碰到一起的时候,她平静下来了。她的痛苦和恐惧开始减弱,我想,这应该和她祖母在死亡集中营的体验太不一样了。我切实的感觉到劳拉开始活跃起来,迎接那些新东西,和我以往不一样东西。我们一起继续安静地呆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空间里。这是一种美好的,安全的静默。咨询结束前的几分钟,我回到我的椅子上,在这个钟头结束的时候,让一切恢复常态。以这样的方式在静默中结束这次咨询,我们感觉都还不错。
在下一次的咨询中,劳拉告诉我,我对她伸出手这件事对她意义重大。当她被触动的那一刻,她说:“我多希望我能坐在你的大腿上。”她告诉我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我想要你为了我,呆在那里,理解我”,她说,她想要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真的坐在我大腿上。然而,这可能是她的力量中相当早期的感受的一部分,这部分正在开始更加鲜活起来。现在我能感受到劳拉信任我,并且她依赖我的共情,依赖我与她的情感连接,这种连接好像一种生命线,就好像我的分析师曾给我的那种共情的想象符号一样。
一次强劲的关系破裂和双向共情的开始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在过去的一年里,那是在七月初。有一次,在咨询前几个小时,我不得不临时取消那次和劳拉的咨询。在这之前,如果我曾经和她取消过咨询的话,我也从没有在如此临近的时间内取消过。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在保持着我们咨询的连续性。两天后,当我们再见的时候,她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安静,有点敏感和沉默寡言。咨询做到中间,她从沙发那边看向我,逐字逐句的吐出一句话:“告诉我,周二你为什么非要取消咨询?你到底告不告诉我?”我犹豫了,不是很确定我该如何回应她,我没有回答。再一次,我发现我自己在自我心理学训练和一个新自体,那个作为一个当下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家,之间摆荡。然而,和上次的例子相反的,这次我选择了旧的,可能是觉得更安全吧,一套靠得住的自我心理学的方法。在老版自体的支持下,我只对她说了这些:“我家里出了点紧急情况。”我有些言不由衷。接下来,我们摸索着去谈其他的事情,继续着这次咨询。接下来,我感受到我们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远离。但我真心地希望并且我有理由相信,我们之间并不是真的产生了远离。然而,那只是我的自欺欺人,很快的我发现我错了。
几分钟以后,她大声喊道:“这不对劲儿!有些事非常不一样!”随后几分钟,她继续保持安静。我想知道这是否会过去,直到她出声:“你真虚伪,你现在很虚伪。你很不对劲儿!”最后的指责激起了关系的,自体心理的自体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做什么也没有用,我感觉到在她面前我是透明的,就好像她能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甚至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能够用她的方式感觉到我的。我鼓足勇气向劳拉坦白:我儿媳妇刚被查出,在她的怀孕后期会有严重的问题出现。我知道,劳拉和她的医学训练会明白我的儿媳妇可能很快就需要一次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并且可能导致很不好的结果。在那一刻,我脆弱的自我碎了一地,我泪崩了。
接着劳拉惊叹道:“我感受到有些什么事不对劲儿!你肯定不好受了!你言不由衷,你对我也隐瞒,我能感受到的。”那一刻,我被我们之间产生的如此快速的真实震惊了。幸运的是,我没有辩解。然而劳拉的专业训练可能早已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我感觉到她的表达比所谓专业关注更好。从一个更新的,更生动的她的一部分,基于在我们一起工作的这几年里,被我们充分滋养的那一个部分,她扩展出一种真正的纯粹的对我的共情。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之间一种新的关系体验,一种双向共情的表达,这让我们都远离技术,而进入了一种人类的深深的情感关系里。我们的新关系现在允许她修通并且可能终止代际创伤的传递,那些她曾经继承下来的关于生命丧失的创伤。
劳拉并不知道,我们的连接过程,帮她穿越了她代际创伤的深渊。这也允许了我,也可能是迫使着我,开始去面对我自己的丧失创伤。那段时间,我和一个有同情心,能高度同频我的分析师-作家见面并开始了咨询。我觉得这个分析师相信我和我的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从我自己的被痛苦地隐藏起来且好像永远失去了的那一部分中,走出来了。正如当我的病人面对创伤性过去的时候不感到孤独一样,当我在这个关于劳拉案例的写作过程中,面对我的创伤性过去的时候,我也并不孤独。因为有包容的存在,在另一个人面前,我就可以向他打开更多,看见更深的悲伤,那悲伤就是,我14岁时,在一次房子失火事件中,我挚爱的父亲意外离世了。我渐渐发现,这个分析师-作家和我一起编写这篇论文,最后我还能够重新开始这个治愈的过程,这个宝贵且令人渴望的,曾被我分析师死亡意外中断了的治愈过程。
在写这篇关于我受到严重创伤病人论文的时候,第一次,我开始寻找我的心声,因为那个深远的发展性的关于我父亲的丧失,曾经彻底地把关于爱的文字从我的心底抹去了。我开始发现我的这一部分,那就是我感觉到自从我的分析师离世之后,我仍然想念他。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新的,加深了的对这些文字的情感,那种情感曾离我那么远。现在,我坚信,我写下的文字,一定是主观的和选择性的抓住了与劳拉和我共享的体验密不可分的特点。我也正在学习,不只是精神分析治疗可以改变分析师和病人,正如Pizer(2000)所描绘,对于具有高度同频他人的分析过程的写作,也能以一种不可想象的和创新的方式,改变和转化分析师。
参考文献
科胡特,H.(1984),精神分析的疗愈之道(A.Goldberg, ed., with P.Stepansk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奥兰芝,D.(2010), 关于心理学对话中主体间脆弱性的思考。intermat. J. Psychoanal. 自体心理学。5:227-243
Pizer,S.(2000), 回礼:写作病人的临床应用。
Slavin,M.&Kriegman,D. (1998/2005),为什么分析师需要改变:在治疗过程中,朝向一个冲突的、协商的和双向影响的理论。关系精神分析,第二卷:创新和发展
作者:Sarah H. Pillsbury, Ph.DSarah H. Pillsbury, Ph.D., is a psychotherapist, psychoanalyst, and couples therapist in private practice in Washington, DC. She is a faculty member of the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Program at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 Psychoanalysis in Washington, DC.
莎拉·皮尔斯伯里博士是华盛顿特区私人执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学家和夫妻治疗师。她是华盛顿特区当代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研究所精神分析培训项目的教员。
Sarah H. Pillsbury 的来信:Li Xin, 理心,
请鼓励你的学生阅读我的论文,并发表评论和/或回应其中的治疗思想和象征意义。我非常欢迎他们的反馈和想法。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interest in my paper and especially for your willingness to translate my paper into Chinese. Below is a recent photo of me.
非常感谢你对我论文的兴趣,特别是你愿意将我的论文翻译成中文。下面(上面)是我的近照。
Please encourage your students to read my paper and post comments and/or respond to the therapeutic ideas and symbolism in it. I would very much welcome their feedback and thoughts.
Best wishes,最好的祝愿,
Sarah Pillsbury, PhD.莎拉·皮尔斯伯里,博士
译者心语
首先,共情一定是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不只是说出来的语言文字。咨询师首先要用心倾听和感受来访,建立情感链接比理性分析更有利于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次,咨访关系里,不只有咨询师对来访者的共情,来访者对咨询师真实的情感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彼此都有疗愈作用。咨询师在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本身也是享受咨询服务的过程。
另外,关于文中提到的作者头脑里产生的位于分析身上正方形的想象符号,我也有类似的体验。那个符号,代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有可能是让人悲伤痛苦的,也有可能是热情温暖或快乐的,也可能是一种复杂混和的情感体验。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无声的定格了的画面,我妈妈的咧开的嘴和整齐的两排牙齿。那个画面不是她在咧嘴笑,而是在一张一合的骂我。骂的内容我没听进去也记不清了,但那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小女孩无奈的逃避式的选择。被骂的原因最初可能是因为她淘气,后来更多的是母亲的痛苦无处宣泄,因为她是老大,因为她的倔强,也可能因为是她一直在主动承担。被骂的时候,害怕,无助,委屈,愤怒等,与两排牙齿这个有趣清晰的画面连接在一起了。
与想象符号类似的,我还想到:有时候一段歌曲的旋律,一种特别的味道,也会和某个记忆里的感受紧紧相连。比如,下班的时候,走路路过住宅楼,闻到熟悉的某种饭香,会产生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因为那是以前我家厨房里经常飘出的味道。
景莉2019年12月25日
微信公众号

理心心理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