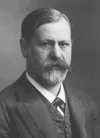对弗洛伊德“trieb”的误解及相关遗留问题的辨析
张腾 刘振
医学与哲学 2022,43(23),43-48
摘 要:
从弗洛伊德经典理论的角度出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弗洛伊德文本,对不同精神分析流派对弗洛伊德理论中驱力(trieb)概念的理解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出弗洛伊德经典理论被混淆的驱力与本能两个概念的区别、分析产生这一混淆的原因、分析了这一混淆会导致的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误解、讨论了对弗洛伊德理论中与驱力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问题,明确驱力概念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梳理了驱力与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本能、力比多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驱力;本能;
1 驱力与本能的混淆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一文中首次引入了“trieb”这一概念,它后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这个概念表示内在于人的一种动力,这点从这个词的词源就能看出:这一词的动词形式是“trieben”,它与英文动词“drive”都源于史前日耳曼语的“driban”,表示从后面推的动作[这也是后来英文中“drive”演变出了“驱动(驾驶)汽车”这一含义的原因]。看起来将“trieb”翻译为“drive”,也即驱动力,无论从词源学的考虑还是从含义上看都是最为恰当的。但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刚刚被引入英文学界时,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trieb”一词相当普遍地被译作“instinct”,而这个词表示的是生物的本能。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处本来就另有一个专门用来表示生物本能的德语词,即“instinkt”,而他一直将此词与“trieb”一词在使用上作严格的区分。“Instinkt”一词在早期的英译版弗洛伊德著作中同样被翻译为“instinct”。显然,从词形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词(instinkt与instinct)的亲缘关系。因为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翻译问题,英文学界、早期一直依赖英译本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中文学界,都对弗洛伊德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误解:两个不同的概念,即“trieb”和“instinkt”被混为一谈了。因此,弗洛伊德关于“trieb”的大量论述,被误认为是在描述人具有的本能的性质。譬如,现在心理学类专业的教科书中常常提及弗洛伊德认为存在着一种“死之本能”[1],而“死之本能”这一概念正是转译自弗洛伊德的“todestrieb”。这个德语概念被弗洛伊德著作英文标准版(以下简称“标准版”)的译者詹姆斯·斯特拉奇译为“death instinct”。高觉敷在其从英文版转译的译著《精神分析引论》(尽管该作是由里维埃夫人译入英文,但同样将“trieb”统一译为了“instinct”)的译序中,就将“死本能”问题称作弗洛伊德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的谬误[2],因为他相信弗洛伊德是从本能的维度来构建精神分析的生死观的;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下,弗洛伊德自然成了一个百口莫辩的悲观主义者。在斯特拉奇之前,也有相当数量的精神分析学者以同样的方式处理“todestrieb”一词和由“trieb”衍生出的其他概念(如1921年在欧内斯特·琼斯的审核下译出的《精神分析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中,译者就大量运用了“instinct”一词,并且显然得到了欧内斯特·琼斯的肯定)。毫无疑问,这个英文译法肯定了“todestrieb”作为一种生物本能的地位。事实上,“trieb”和“instinkt”虽然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却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在弗洛伊德那里,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组相对立的概念。为了避免混淆,本文的以下部分除了引用他人译文或论述中的表述,都会使用“驱力”一词作为对“trieb”的翻译,这不仅是为了遵从德语词“trieben”推动、驱动的原意,选择这一翻译、排除其他翻译的其他原因也会在后文中说明。
我们可以考查弗洛伊德著作最完整、影响最大的英译版本-即标准版-中译者为弗洛伊德关于“trieb”这一概念的重要论文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所作的序。在1957年出版的标准版第14卷中,斯特拉奇将此文译作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在这篇对“trieb”这一概念的专论中,斯特拉奇仍然使用英语单词“instinct”来翻译弗洛伊德的术语“trieb”;但显然,英文中的“instinct”一词的含义与德文中的另一个词才是更相近的,即前文所提及的“instinkt”。“Instinkt”一词在德国生理学中被用来描述动物那些先天具有的行为趋向,即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弗洛伊德也常在描述动物的先天行为时审慎地使用这一词-在描述这些现象时,他并不使用“trieb”。换句话说,他一直小心地强调:“trieb”这一概念与动物或人的本能并不相同,他不愿将两者混为一谈。
事实上斯特拉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譬如,他在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的编者导言中指出,自己“在此使用此词(指他用于翻译‘trieb’的‘instinct’一词)所表达的涵义,与当下生物学家的用法并不相同”。但他紧随其后又矛盾地声称,尽管他在译文中借由“instinct”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与流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并不相同,但他仍然决定选用此词来翻译弗洛伊德的概念“trieb”。他认为这一选择并不是翻译上的失当,而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赋予此词的含义让我们(不得不)如此翻译此词”[3]。
这就是说,尽管斯特拉奇知道这两个词在德语和英语中并非是对应关系,但他在阅读了弗洛伊德关于“trieb”这一概念的论述后,仍然认为弗洛伊德所试图描述的被称为“trieb”的内容在英语中使用“instinct”一词来表达更为贴切。他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弗洛伊德在使用“trieb”和“instinct”的谨慎,却又微妙地将其故意忽略了。换言之,毫无疑问,即便斯特拉奇意识到驱力与本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他也认为,在精神分析中对驱力和本能是可以作相同处理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弗洛伊德“后来在《论无意识》(Das Unbewusste)一文中自己也用过‘instinkt’这一德语词,不过意义与此处被我翻译‘trieb’用的这个‘instinct’又大不相同”[3]。这也再次证明了,斯特拉奇深知弗洛伊德用以表示动物本能的词语“instinkt”指的是与驱力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翻译者本人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区别,但他却放弃了将这种区别在文本中体现出来。这种处理方式让译作的读者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本不该有的误解,这便深深影响了后来英语学界和中文学界的弗洛伊德研究。
那么,这个与生物本能所不同的“trieb”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从其德语词的原意来看,它毫无疑问指的是一种推动力,来促使主体去采取某种行动。从这点上看它们是相似的,因此,笔者将尝试论述包括斯特拉奇在内的一众精神分析研究者将这两个概念混淆的原因。
2 产生此混淆的原因
从上文来看,驱力和本能两个概念的确具有一些相似的性质:他们都是一种动力(instkint的词源为拉丁语动词instinguere,表示驱使、鼓动,但后来已逐渐流变为本能、固有冲动之意),同时,这种动力都不是来自于主体的意识层面。换句话说,它们都不是出于主体的意志;恰恰相反,是它们支配了主体,就像饿的时候动物会在本能的支配下自觉去觅食一般。
事实上,弗洛伊德在1926年的著作《压抑、症状与焦虑》(Hemmung,Symptom und Angst)中,表示小汉斯的动物恐惧症与其他哺乳动物畏惧雷雨的本能(instinkt)表现是相似的;但作为人类特有的恐惧症,它“与那些被失落的对象有关”。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小汉斯对马的恐惧时大量使用了“trieb”一词,但在将这一症状与其他动物类比时、在对动物现象的描述中使用了“instinkt”。毫无疑问仅这一则文本就足以说明,弗洛伊德已经将这两种动力做了明确的对比与区别:相对于作为动物之“本能”的“instinkt”,“trieb”显然是在后天生活中被结构的-不然它无法按照弗洛伊德的表述,同那些后天的“失落的对象”产生关系。
如同斯特拉奇所提及的,在《论无意识》中,弗洛伊德也使用了“instinkt”一词。他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心理学与遗传学的关系,这些相关的讨论后来对荣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论无意识》中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有某种类似于动物之本能(instinkt)的东西存在于人类中”?这就证明,弗洛伊德试图填补的一个理论空缺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它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动机,如本能一般支配人的行动,同时又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一种代代相传的迹象-就如同动物本能的遗传一样?也许正是因此,斯特拉奇才把驱力与本能两个概念混淆了。然而,弗洛伊德在此所说的这种代际的传递性,又与遗传有着天壤之别:在遗传的过程中,显然是同一种本能被传递了,换言之,本能作为一种推动力,总是推动着每一代生命去做相同的事(如觅食、繁衍);而既然推动小汉斯逃避马的那种力量(即驱力)与小汉斯成长过程中失落的对象有关,驱力就必然由于每个人所遭遇的阉割各不相同,而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显像。譬如,在小汉斯个案中,它表现为对马的逃离;而在施瑞伯的案例中,它表现为对上帝疯狂的热爱等。
在此,通过弗洛伊德本人的两则文本(《压抑、症状与焦虑》和《论无意识》)中用词的差异,我们已经明确了驱力与本能之间的区别。尽管驱力(与本能一样)是主体无法克服的一种冲动或动力,但它与本能仍然天差地远:本能并不会因为主体的经历有所改变,而驱力则完全不一样。它既然与主体所失落的对象有关,我们就可以说,实际上,它是由主体的生活史塑造的。因此,虽然它与主体的经历可能在表现上并不明晰(如小汉斯对马的恐惧实际上来自对阉割的恐惧),但它本身与主体经历的关系是不容否认的,这才使得它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落脚点。
值得一提的一个角度是,斯洛文尼亚的拉康派学者萨摩·汤姆西奇在其著作《享乐的劳动》中表示,弗洛伊德本人也促成了斯特拉奇的这种误解;因为弗洛伊德的早期研究是从“禁止”“压抑”“抑制”等一系列具有否定性的概念出发的,因此,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实际上模糊地存在着一组对立,即“禁止者与被禁止者”的对立。既然禁止者是人造的象征秩序,那么被禁止者自然就是有别于象征秩序的,因而斯特拉奇会把被压抑的驱力理解为自然的、本能的。汤姆西奇认为,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批判弗洛伊德“压抑性的预设”,也是出于此同一种误解。汤姆西奇补充道,驱力的确有别于象征秩序,但它并非是在象征秩序之先(也即并非是本能的),而是象征秩序的具体产物。在这一点上汤姆西奇是忠实于弗洛伊德的:他并不把驱力当作一种本能,而认为它与主体与象征秩序的关系,即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过程中的经历有关[4]24。
幸运的是,随着中文学界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推进,这个存在问题的翻译传统已经逐渐被打破;前文提及的弗洛伊德名篇Trieb und Triebschicksale,已在近年被中山大学知名的精神分析学与哲学研究者卢毅从德文原文重译为《冲动与冲动的命运》-此前这篇文章在中文学界只有来自英译本的转译版本,依据其在标准版中的英译版本被译为《本能及其变化》。将“trieb”重译为“冲动”无疑是一个进步:它表示中国的精神分析家们不再把驱力作为一种本能来理解了,譬如,至少不会认为弗洛伊德坚信人有一种求死的本能。事实上,笔者推测“冲动”这一翻译很有可能受了法国精神分析传统的影响,因为法语学界也常常用“pulsion”来翻译“trieb”一词。拉普朗虚等[5]在《精神分析词汇》中就提到,法国精神分析界早期同样用“instinct”(与英语词instinct同形的法语词)来翻译“trieb”一词,但后来法国精神分析家艾斯纳提议使用“pulsion”一词作为对“trieb”的翻译,推翻了旧的译法。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拉康派精神分析研究者也常将“trieb”译为“冲动”,这个词更近于法语“pulsion”之意涵(但拉康曾经还提及可以将之译为法语词“dérive”,这个词意为“漂移、偏斜”,显然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表示主体中不可控制的一部分,而这个词又与英文的“drive”恰巧读音相似[6])。然而笔者在这里仍然会采用“驱力”而非“冲动”作为对“trieb”的翻译。毕竟“驱力”与“冲动”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而笔者认为,前者更能反映主体被驱力影响、支配的被动地位。因此,除了对既有的将“trieb”译为“冲动”的文本的引用,本文不会将“冲动”和“驱力”作为同义词使用。
3 驱力、本能与力比多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那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力比多(libido),它被译为性力、欲力等。这一概念同样出自《性学三论》中,甫一诞生就与驱力、本能两个概念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显然,这些不同的意译都表明,弗洛伊德对这一术语的运用范围是相当狭隘的-与作为一种广为存在的精神现象的驱力有别,力比多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仅仅是一个性学概念(尽管在《性学三论》的导言中,弗洛伊德曾经申明,精神分析中性的概念实际上与哲学中的爱更为相似)。
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理论中就开始大量运用力比多这一概念,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过相当精确的解释。他只是表示,“力比多”在性上的地位,同“饥饿”在营养上的地位是相当的[7]135。然而“饥饿”-也即进食的冲动-并非纯粹是为了营养。弗洛伊德本人就将暴饮暴食(乃至吮吸或抽烟这些并非是进食,而只是模仿进食动作的行为)与口欲期所遭遇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说,饥饿并不只有本能的,也有驱力的。不只有为了延续生命而存在的本能的进食冲动,也有固着在某一个特定对象上的进食冲动、作为症状的倒错性进食冲动,甚至是不进食的冲动。同样的理论也可以套用在性行为上:不只有为了实现繁衍目的的本能的性冲动,也有固着在某个特定对象上的性冲动、作为症状的性冲动,甚至是对性的弃绝和厌恶。因此,力比多这一概念,就同时包括了“性本能”与“性驱力”。笔者认为,这正是弗洛伊德将力比多与饥饿的这一类比放在《性学三论》的首篇(《性变态》)开头的原因。
在《性学三论》的《力比多理论》一节中,弗洛伊德给力比多下过一个事实上相当模糊的定义。他说:“力比多,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可变的动力,它是可以量化的,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性兴奋领域中的进展与转变。”[7]217据此,我们可以这样廓清力比多在弗洛伊德理论当中的地位:这一概念被引入,是为了描述一切性方面的冲动,我们不仅可以用它描述性兴奋的强度,也可以描述性兴奋的对象。它既包括先天的、本能性的性冲动,也包括后天的、被视作“性变态”的性冲动。也正是因此,在《性学三论》的《力比多理论》一节中,他还进一步地提出对象力比多这一概念。这说明,他把具有特定对象的性冲动当作一种特殊的性冲动来研究。因为,在弗洛伊德处,本能是没有特定对象的;而他在《性学三论》中又将对象定义为驱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同样地,根据上一处引文,弗洛伊德指出,力比多是可变的。换句话说,它可以受到主体后天的遭遇的影响,这也与弗洛伊德对驱力的可变性的描述相符合。
既然性冲动和其他冲动都遵循同一种范式-它们都可以分为本能的和驱力的(如动物躲避雷电的冲动和小汉斯躲避马的冲动)-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仅仅在性领域提出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词来描述冲动呢?毫无疑问,这当然和弗洛伊德对性学的格外重视有关。事实上,在《性学三论》创作时期,在如何评价性学的地位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分歧已经相当显然了。在此文中,弗洛伊德表示,虽然力比多理论还停留在猜想的阶段,但“如果我们效仿荣格的做法,将力比多的概念视同一般的心理驱力,并因而淡化它本身的意义,那我们迄今为止从精神分析的观察中获得的一切便都付诸东流了”。弗洛伊德对性学的重视,当然可以用其时代背景来解释-其他的理论是如何忽视了性的重要性云云,然而,本文试图论证的是,弗洛伊德对性学的这种偏重,并非仅仅出自其个人的偏嗜,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蕴含的一个观点,即,一切驱力都是性驱力(同样地,一切驱力也都是死亡驱力)。这一点,是弗洛伊德本人并未注意到的,因此才遗留下了关于驱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4 驱力与主体的关系
前文已经说明,在弗洛伊德处,本能和驱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死亡驱力这个概念最能说明这种区别:本能总是在乎着主体的生命-摄食、饮水、繁衍等本能都是为了延续生命或种系而存在的,而且它懂得如何在过度时调节自身;而驱力则并没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方向:它作为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推动着主体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而它的目的究竟是哪里,不仅主体可能不知道,甚至连驱力本身都并不在乎。就如厌食症患者,他们对进食的弃绝,导致他们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面临死亡的危险,这种死亡的危险当然不是清醒的患者本身想要的,但他们无法抵抗自己这种否定性的心理动力。换句话说,驱力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目的。它虽然诞生在主体身上,但是并不轻易屈从于主体的意志。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也可以知道这点:驱力的命运有以下四种:反转为自身的对立面、转向自己本人、压抑、升华;这其中显然没有一条的含义近似于“因得到了满足而平息下来”。驱力的诸种命运,卢毅所译《冲动与冲动的命运》表达得相当清楚,本文不需要再赘述;但其原文用词仍然是值得考察的:弗洛伊德用“schicasale(命运)”一词来描述驱力可能遭遇的变化,就说明弗洛伊德有意将驱力作为一种活物来描述-这并非是一种捕风捉影,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第三十二场精神分析讲座中,他还提出了一个更直白的概念“triebleben”,即“驱力的生命”[8]90。
弗洛伊德为何如此强调驱力是有生命的呢?我们先来考察弗洛伊德在《冲动与冲动的命运》当中的一则说明。弗洛伊德提及“(如果干渴与饥饿的感觉让自己被感觉到的过程,是干渴与饥饿这两种感觉所需要的器质性基础),那么食道黏膜的干涩或胃黏膜的腐蚀让自己被感受到时,无疑就是冲动(驱力)刺激”。因此我们首先可以知道这一点:当我们把驱力作为一种刺激来分析时,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隐秘的需求让自身显像的过程。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是某一种情结以一种特定的性冲动为形式,对主体产生影响、令其产生冲动的过程;且这一对精神的刺激必然来自主体的内部(尽管它的根源是主体与外部有了某种遭遇,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情结,但其作用于主体的过程是在主体的内部完成的)。至此,驱力至少变成了“有机的”,因为它作为一种内在反应,必须依托于主体的生命;但它离“有生命的”仍差一步。在这里,弗洛伊德再一次用饥渴的感觉与驱力相类比,这就为驱力究竟能否被满足这一问题划上了一个问号-尽管弗洛伊德在此文中曾表示“冲动的目的总是满足”(这一表述与其本人的另一些论述是相悖的,然而这并非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弗洛伊德对本能和驱力的区分:如前所述,他强调驱力是一种对精神的推动、一种强加于精神的力。因此,可以得到这一认识:驱力表现自身至少需要一个主体-在精神分析理论当中,也可以说,就是至少需要一次阉割。而本能,则并不需要主体的介入,或者可以说,不需要一个精神分析意义的主体的介入。某种意义上,“本能”更像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并且知道如何调节自身。但也正是这个意义让它不再需要主体。或者,更恰当地说,本能并不是与主体有关,而是只需要一个“生命体”就行了。那些没有经历过阉割、没有原初失落的动物,仍然能够在本能的支配之下行动。驱力,由于其形成就与主体的遭遇有关,自然只能依附于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体。虽然对那些动物来说,存在着客体关系学派所言及的“主体意象”与“客体意象”,但并没有任何工具为这些意象赋予意义,分析家与这些动物无法通过一个媒介展开沟通,因此,从临床的角度上,它们也不是可被精神分析的主体。弗洛伊德之所以强调小汉斯的动物恐惧症与原初失落的关系,原因就是这样:小汉斯对马的恐惧归根结底是(由于其俄狄浦斯情结而诞生的)对阉割的恐惧;他产生的逃离马以保护自身的冲动,实际上是逃离阉割的驱力的变形-这就是说,我们为驱力又新增了一个特征,即它在形式上是可以被另一种驱力取代的。由于不直面阉割的动机,精神装置中发生了对阉割的移置(verschiebung,displacement)。因此,弗洛伊德才将小汉斯的恐惧症归为一种防御机制。这照应了他在《冲动与冲动的命运》中的叙述:“考虑到抵制冲动直接延续的动机,人们也可以把冲动的命运描述为防御的类型。”[9]换言之,主体在意识层面抵制着驱力的直接表现,因此需要内在的防御机制来改变它的表现。既然驱力有别于不需要主体的本能,而是后天被结构的,并与那些失落的对象有关,那么它就必然和主体的生活史有关。换句话说,也就是与主体所遭遇的阉割有关,无论这些阉割是以何种形式发生的、又是否完成了。我们在此可以重新定义驱力:主体的生活史(如“阉割恐惧”史)造就了那个名为“驱力”之物,它让主体感受到自身的运动趋向(即无意识的动机),而并不顾及主体个人在意识层面的意愿。
从某种角度上讲,驱力就像肿瘤一样:它本身是身体内自然的精神活动现象,但由于致癌因子的影响(主体遭遇了某些对象的失落),它成为了一种异质性的寄生之物。它有自己的生命,让主体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但并不在乎它是否给主体带来了痛苦,更不在乎自己是否可能会导致主体的死亡;此外,它还可能在免疫系统(防御机制)的影响下发生诸多改变。它也可能表现为纯粹良性的,并不会对主体产生恶性的影响,不会导致主体遭遇特别的痛苦,也不会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没有去做精神分析工作的必要。而且,它还形成了主体独特的性格特点,参与了人格的发展。
5 作为人与动物区别的驱力
根据上文的论证,我们可以重整弗洛伊德关于“破坏性的驱力”的论述:虽然弗洛伊德认为有些驱力的目的是破坏,但破坏也许恰恰不是这些驱力的目的(不是它们最在乎的东西),而是它们最不在乎的东西-驱力在追求自身的满足的过程中,并不在乎其过程是否会导致破坏。这就可以解释弗洛伊德曾经留下的一个问题,他疑惑为何“破坏性内驱力中也含有性爱成分”。答案是,并非是破坏的驱力包含了性的成分,而是性驱力将自身表现为具有破坏性的。诸如施虐、受虐这些破坏特定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他者还是主体自身)的过程并非那些驱力的目的,而是它们寻求满足所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同时也解答了弗洛伊德的另外两个问题,即“这两种驱力在生命过程中是怎样混合在一起的”“死亡驱力是怎样用来为性爱的目的服务的”[8]101。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性驱力和死亡驱力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与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发展上重要的一步是相似的。刚刚提及的两种驱力-即与性欲相关的驱力(弗洛伊德有时将其称为生命驱力,即lebenstrieb)、与破坏相关的驱力(即死亡驱力todestrieb)两个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你死我活、两相对立的,一者的胜利象征着另一者的失败。然而这组对立,其实已经是弗洛伊德对他的驱力理论作了修正的结果。弗洛伊德早期认为,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驱力,但最初他觉得这两种驱力是“性驱力”与“自我驱力”。他后来又察觉到,自我保全的欲望本身也可能与爱欲相关,于是他将“自我驱力”并入了“性驱力”,称为“性驱力”(或“生命驱力”),并将它与“死亡驱力”相对立。同样可以将性驱力并入死亡驱力(或者恰恰相反-将死亡驱力并入性驱力),因为性驱力也可能导致死亡的结果,而死亡驱力也是源自爱欲。说性驱力可能导致死亡的原因,前文已经作出了解释;而说死亡驱力也是源自爱欲的原因,则是因为,驱力总是以某种方式折射出了主体所遭遇的特殊的阉割、反映出主体对失落对象的情结。用汤姆西奇在表达相似的观点时所说的话,这便是“每一种话语都是享乐的话语”“每一种驱力都是死亡驱力”[4,5,6,7,8,9]。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弗洛伊德处,驱力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成为了人标志性的一个特征。首先是有阉割、有原初的压抑-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无意识”诞生的时刻,这标志着主体的诞生。伴随着那个原初的失落,主体形成了一种情结、一种爱欲,这种爱欲落实到行动,就表现成一种无意识的动机,即驱力。然而,那个失落的对象,与因它所形成的驱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可能是隐秘的,因为驱力有可能不得不受到压抑,而以另外的形式表现起来,使它无关于那个原本的对象。在这个维度上,驱力不仅反映了内部(主体所受的阉割)和外部(外在对象的失落)的沟通,同时也模糊了主体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因为外部的阉割、创伤和失落最终成为了主体精神现象的一部分)-而弗洛伊德本人则早早就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性学三论》中将驱力描述为“心灵和身体之间一个交界的概念”(此处又可以证明弗洛伊德反对把驱力理解为一种身体的本能)。因此可以说,驱力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把人类行为的动机同动物的一般本能区别开来。这一“病理性”的特征常常成为精神分析实践的对象,然而它却可以被用来定义人。
6 驱力的生产性特征
前文论述了弗洛伊德处“驱力”和“本能”这组概念的对立。通过把驱力与一般的本能对立开来,弗洛伊德明确了驱力与失落、阉割等概念间的关系,也澄清了驱力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对象的重要意义。至此,方可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重视驱力、这个概念为什么在他的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直到生命的终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讨论。弗洛伊德不仅强调驱力与本能的对立,也强调不同驱力之间的对立。正如前文所述,弗洛伊德早期提出了生命驱力与自我驱力的对立,又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将其修订为性驱力与死亡驱力的对立。本文已经论述了性驱力与死亡驱力实际上的同一性,这是否意味着本文的立场是如荣格一般,含混地将一切行为的动机整合为一种“生命能量”呢?答案并非如此。笔者仍然如弗洛伊德般坚持驱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但本文并不是要像拉康派学者一样,去讨论一种驱力中存在的两种倾向的分裂,亦或是去讨论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对立;也不是要像哲学家约翰斯顿一样,讨论驱力如何在时间轴上分裂。本文强调的是这样一组对立:驱力-因为其生产性-导致的它与自身的对立。
尽管在很多精神分析家之处,驱力究竟是否有明确对象这个问题仍然存疑;但本文在此持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立场,即驱力有四个要素:压力、目的、对象、来源。前文已经提到,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驱力是一种混淆了身体与心灵、连接了内部与外部的概念。无论驱力是否得到了满足(本文中并不会讨论驱力的可满足性),甚至,无论驱力是否成功让主体采取了现实的行动,作为一种刺激,它都对主体产生了精神的作用。如若一种驱力真正得到了满足,或是被防御机制改变了形态,那么显然它会制造一种新的失落:在原本的位置上,有一个驱力消失了。从驱力与失落的关系上看,驱力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作为一个对象被失落,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驱力被生成;换句话说,即便神经症患者表面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他的症状也未必会停止。如果一种驱力并没有被满足,那么,由于驱力与它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尚未被填补的空缺,神经症患者就被赋予了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为了弥补这种失落,无意识不仅要生产出一种驱力,让主体在现实中从事某种行动,来填补这种空缺;同时,原本的那个驱力由于迟迟得不到满足,更会随着压抑的时间延长而越来越强。
因此可以说,驱力既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介入了主体的心理现实,它便总是在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生产性的效应。一旦主体感觉到驱力的存在,那么,不管它是否被实现,驱力就已经开始扮演了生产性的角色。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驱力的存在,才让一个人采取了本能以外的行动,他的主体性才能在现实的意义上实存。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关系,驱力实际上成为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正是因此,弗洛伊德在《驱力与驱力的命运》中才强调,驱力实际上是一个在主体内部发挥作用的过程、一种内在于主体的机理,甚至是主体的组成部分。
理解这一点后,我们反而可以回顾斯特拉奇将“trieb”翻译为“instinct”这一错误背后可能的用意-因为他已明确表示,采取这种并不严格对应的方式来翻译,是他自己有意为之。在斯特拉奇那里,精神分析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还没有联系起来。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对那些动物来说,虽然在它们那里存在着主体意象、客体意象等一系列概念,但这些概念并没有被语言赋予意义;我们无法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对动物开展精神分析,因此,动物也就不能够成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主体。但在斯特拉奇处,由于语言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尚不明确,普遍的生命体和主体的区别就也没有被明确。他对主体中驱力的理解,就如对生命体中本能的理解一般:既然驱力是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必然是“先天”地对主体产生行为上的影响。因为如若没有驱力就没有主体,是驱力(偕同其他组成部分一起)让主体进入了实存,反过来说,主体的诞生必然伴随着驱力的显像;就如生命体在诞生之初就受到本能的支配、生命体的行动反映着支配着它的本能一般。因此,斯特拉奇对驱力与本能的混淆事实上反映出了其对精神分析实践的主体与纯粹的生命体两者的区别的模糊。然而,虽然当时语言学尚未被正式引入精神分析领域,语言这一媒介的重要性却是弗洛伊德很早就强调过的。弗洛伊德很早就论述了词表象与物表象的关系。在小汉斯个案中,他更是讨论了小汉斯的恐惧对象是如何通过语词的相似性被移置。理解了斯特拉奇对驱力的先天性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弗洛伊德在驱力理论中首先提出的是“生命驱力”,并在后续的理论修改中都强调生命驱力的重要地位。
驱力对于主体犹如一种“汝当如此”的内在勒令,首先是压抑了主体的一部分自由。它对自身以外的精神活动的排除,也生产出了新的无意识-或者说,它把更多的东西赶入了无意识,以此挤出空间、让自身得以显现。这个过程意味着更多东西作为意识表象失落了,也意味着更多驱力的生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会有诸多驱力在意识区域杂乱地活动,因为,正如《冲动与冲动的命运》当中弗洛伊德的论述-压抑反而是驱力最常见的命运。由于这些压抑既不具有剧烈的创伤性,也不如原初失落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所造就的驱力也就必然没有那么强烈。因此,要去讨论它们遭遇诸种命运之后所造成的影响,也就未必十分有意义了。
本文得出的结论中最重要的是,驱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其生产性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一种驱力总是生产出一种或更多种与自身对立的驱力,这样一来,如荣格般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中的对立精神产生误解,并因此不得不将一切行动的动机从对立着的驱力整合为一种统一的、同质的生命能量的道路便被否定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弗洛伊德驱力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核仍然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参考文献
[1] 杨凤池.咨询心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26.
[2]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xxii.
[3] FREUD 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 XIV[M].STRACHY J,trans.London: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57:111.
[4] TOMŠIČS.The Labour of Enjoyment:Towards a Critique of Libidinal Economy[M].Berlin:August Verlag,2019.
[5] 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词汇[M].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1:385-390.
[6] 埃文斯.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词典[M].李新雨,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86.
[7] FREUD S.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 VII[M].STRACHY J,trans.London: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53.
[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M].郭本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 卢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冲动与冲动的命运[EB/OL].(2015-12-18)[2022-05-02].https://www.douban.com/note/529638594/.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