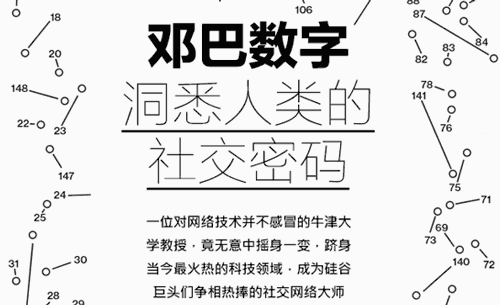差不多十年前,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开始研究英国人寄圣诞卡的习惯。在邓巴做研究的那个年代,社交网络尚未诞生,他希望找到一个办法衡量人们的社交关系。邓巴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认识多少人,他还想知道每个人真正在乎多少人。他认为,探寻这种情感纽带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圣诞卡。毕竟送卡片是种投资:你必须知道邮寄地址,去买卡,得写上几句、买邮票、然后寄出去。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为无足轻重的人这样费心费力。
邓巴与人类学家拉塞尔·希尔(Russell Hill)研究发现,人们约四分之一的卡片寄给了亲人,近三分之二给朋友,8%给同事。不过,最主要的研究发现是这样一个数字:以一个人寄出的全部卡片为例,所有收到贺卡的家庭的人口总和平均为153.5人,也就是150人左右。
这一数字与邓巴的预测十分吻合。在过去二十年中,邓巴发现,以150人组成的团体随处可见。人类学家在研究至今尚存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时发现,一个宗族通常有150名成员。纵观西方军事史,最小作战单位“连”通常约有150人。以Gore-Tex等创新产品著称的材料生产企业戈尔公司(W.L.Gore&Associates)也拥有类似的办公架构。当一个分支机构的员工超过150名时,戈尔公司就会将他们一分为二,再建一家新的办公室。
在邓巴看来,原因很简单:就像人类无法在水下呼吸、两秒半内跑不完百米、用肉眼看不到微波那样,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实质关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从认知角度来讲,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与人类的其他特性一样,这一规律亦有例外,有宅男宅女,也有像比尔·克林顿那样的人。但总体来说,一旦一个群体的人数超过150人,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淡化。虽然现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人类的社交能力与石器时代没什么两样。邓巴写道:“150人似乎是我们能够建立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了解他们是谁,也了解他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虽然邓巴一直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但如今他却在一个特殊群体中声名鹊起——开发社交网络的硅谷程序员。Facebook以及Asana和Path等科技公司都试图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交关系移植到网络空间并将其扩大,此时邓巴的研究观点经常得以引用。软件工程师和设计者纷纷将他们的想法建立在所谓的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之上。成立于2010年的Path是一家以移动方式提供图片分享和消息服务的公司,它显然是运用了邓巴理论——它设定每个用户至多拥有150名好友。Path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戴维·莫林(Dave Morin)说:“邓巴的研究表明,无论科技怎样进步,我们终归都只是人,都逃不开人类的极限。”对莫林来说,邓巴坚持的人际关系上限论对Facebook等社交网络的理念构成了挑战,在Facebook上,你可以拥有数千名好友。邓巴的研究帮助社交媒体设计师们在有关设计技术能否扩容个人社交空间的辩论中厘清了头绪。正如邓巴所说:“问题在于,从通常意义上来讲,数字技术能否让人们在维系老朋友的同时,结交新朋友,从而扩大整个社交圈子。答案似乎是一个响亮的‘不’字,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
现年65岁的邓巴有些发福,不过,他在上楼时依然喜欢一次跨两级。他是牛津大学教授,任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去年11月的一天,邓巴和我讲述了他的故事。邓巴在坦桑尼亚长大,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邓巴在十几岁的时候喜欢在海边潜水,还曾开车到丛林里猎杀大象。上世纪70年代初,邓巴是一名研究生,当时他的研究兴趣并非人类的友谊,而是狮尾狒的社交生活,这一猴科动物唯一的栖息地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它们与狒狒是近亲。
在邓巴冗长的讲述中,他的嘴角有时会泛出一丝冷冷的浅笑。在讲到狮尾狒的什么特点吸引了他时,他说:“是它们社会体系的独特性,若干小家庭团体组成了一个大的狮尾狒族群。这与现代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有些类似。这是一种裂变—融合型的社会体系,在除人类以外的约上百种灵长目动物中,只有两种猴科动物过着这样的生活。”
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狮尾狒梳理毛发的习惯。与其他许多灵长目动物一样,梳理毛发对它们来说不仅仅与清洁有关。这也是它们建立关系的方式。狮尾狒的生活中充斥着尔虞我诈,这里有阴谋团体、有篡权政变、还有帮派结盟。狮尾狒通过为彼此剔除毛发中的寄生虫、揉捏皮肤来巩固交情。邓巴早年的论文中指出,狮尾狒梳理毛发的时间并不取决于其体形大小——如果取决于体形则说明梳理仅仅是出于清洁目的,因为体形越大所需时间越长;实际上,梳理时间取决于族群大小,群体越大耗时越多,因为成员们需要通过按摩来彼此讨好。
1992年,邓巴公布了新研究结果:大脑的大小也与族群规模有关。在科学界,灵长目动物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脑袋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大脑袋对能量的需求很高,而且要好几年才能发育成熟,此外,保护大脑的头骨变大也令分娩过程更危险。
邓巴在《人类进化杂志》上撰文指出,灵长目动物之所以进化出更大的脑组织,是为了解决社会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集体生活虽然好处很多,最明显的是可以更好地抵御掠食者,但是族群成员相处也并非易事,要围绕食物和配偶展开竞争。它们要抵御一些族群成员的恐吓和欺骗,同时还要恐吓和欺骗另外一些成员。邓巴解释说:“群体生活是解决特定生态问题的适应性手段,这对社会型动物来说都一样,对灵长目来说尤其如此。但群体生活本身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契约难题:有些成员会在你刚刚找到食物时就把它偷走。”
随着群体规模扩大,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也大得令人头疼。在一个有五位成员的群体中,成员间共有十组双边关系;在20个成员的团体中,双边关系数量上升到190组;50个成员的团体则升至1225组。这样的社交生活需要强大的大脑。邓巴在1992年的论文中指出,大脑皮层越大,它们所能应付的群体规模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即便是最聪明的灵长目动物——人类,也不具备在一个无限大的群体中所应拥有的处理能力。为了预测人类群体的规模上限,邓巴将人类大脑皮层的占比数据纳入图形进行分析,得出的数字是:147.8人。
虽然此前也有其他学者主张可以用社会学来解释高等智力的发展进化,但邓巴简单的算法——较大的头脑等同于较大的群体,令其观点引发共鸣,如今,邓巴被视作“社会脑假说之父”。麦吉尔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西蒙·雷德尔(Simon Reader)说:“他的观点非常有影响力,已成了当今的主流假说。”
“邓巴数字”使邓巴成了名人。他近期的著作大多都受到追捧。他曾在科技、娱乐与设计(TED)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为科学界以外的普通读者写书;最新的一本书名为《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ove),去年11月在美国出版。
邓巴与人相处时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既不是因为孤僻,也不是因为害羞。在旁人看来,邓巴并不热衷于多结识一些人。当被问到“作为一个社会行为学者,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时,他答道:“我差不多处于中间水平,但我显然不属于过度交际类型的,这一点很肯定。”在整个下午,他曾被两个电话打断。第一个是一个大型图书节邀请他作发言嘉宾,第二个是BBC新闻网邀请他在同一天晚上参加一个节目。邓巴对这两个邀请都表示了拒绝,对第一个还带有一丝厌烦,他后来解释说,之前他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表示了回绝。
邓巴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他现在正在和语言学家、计算机学家、经济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等展开合作。这些项目都与社会脑假说有关。其中一个项目研究的是笑容的生理作用,以及它在巩固社会纽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另一个项目的研究对象是舞蹈。邓巴的合作伙伴对他交口称赞。他的合作者、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菲力克斯·里德-索察斯(Felix Reed-Tsochas)说:“罗宾是那种不到五分钟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喜欢上的人,他满脑子都是有趣的主意,会让你为之一振。”
2010年秋天,邓巴接到了莫林的电话。莫林曾是Facebook应用平台的负责人,2010年初他离开Facebook,成立了Path公司。早在几年前,莫林刚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主修经济学时,他就注意到了邓巴的研究成果。
莫林说,Path可以让所有人都做到这一点。它提供的服务能让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发布照片,用户可以互发评论,并搜寻其他人的信息。一个更具亲密感的功能可以让用户告诉他/她圈子里的所有人自己何时入睡何时起床。但是这个圈子的人数不能超过150人。说到底,Path是为“圈子”而建。
莫林说:“人们觉得他们可以把不能在别处发布的信息放到Path上来。从根本上来看,150人是一个人交友记忆的上限,一旦超出,你就会开始进行信息过滤,调整你所分享的信息内容,此时,你就是以公共面目示人了。”目前Path已拥有超过500万用户,莫林说,由于控制了社交圈的人数规模,公司的活跃用户数量相当可观。
莫林与邓巴的第一次会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当时谈论的话题包括,普通友谊在缺乏面对面沟通时可以持续多久(邓巴的研究答案是6到12个月),以及为什么在邓巴看来,女性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包括她的爱侣),但男性只能有一个。此后,两个人每过几个月就会沟通一番。Path所使用的寻找用户好友的算法就是基于邓巴的研究。莫林表示,公司今年还将推出几项源于邓巴观点的全新服务功能,不过他拒绝对此详加描述。
莫林说,单独拿出一个邓巴数字可能会造成误解。邓巴实际上给出的是一系列数字范畴,限制了人际圈子的无限扩大。最核心的圈子可能有三五人,是最亲密的朋友。然后是12到15人,这些人去世的噩耗会带来重创。然后是50人,邓巴在所著《你需要多少朋友?》一书中写道:“50人通常是大洋洲和非洲土著居民等狩猎采集型社会中,集体在外过夜的人数规模。”至于150人之外则有一些更大的圈子:举例来说,狩猎采集型社会的部落平均有1500人,他们讲同样的语言或方言。邓巴通过调查和人种学研究发现,这些数字大约以三的倍数增长,至于原因,他也不是很清楚。
风险投资家杰里·默多克(Jerry Murdock)是Path的投资者之一,他所供职的公司Insight Venture Partners还投资了Twitter和Tumblr。默多克在这一问题上的解读颇具数字命理学色彩,他认为邓巴数字就是一个社交领域的斐波那契数列,这个简单的数学关系揭示了更为深奥的宇宙真理。他认为这两组数字或许彼此相关。默多克说:“与所有伟大的理论一样,邓巴理论解释的是限制,即自然存在的限制。而正是限制造就了伟大的架构和伟大的公司。”
简单易懂的特性令邓巴的观点广为人知,但这同样令他面临着研究过于简化的指责。微软的网络理论家和研究科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表示:“这么做实际上是用单一理论将大千世界简化为一个维度和一个数字。”在沃茨看来,作为一系列亲密关系圈,邓巴的友谊模型显得太过简单,他认为,在真实世界中,人们有的并不是较好和较差的朋友,而是需求不同,朋友类型也就不同。沃茨说:“如果你跟我说,只有150人比较重要,那我问你,对哪些方面重要?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高中老友,可能是你当前的社交圈,也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具体想要什么。社交网站面临的挑战正是去解决这一问题。”
以人类学家和大脑研究科学家为首的其他人则对邓巴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邓巴的理论或许没有充分考虑到推动人类大脑增大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我们的先祖必须要以更有效的方式去寻找食物,或是必须在动植物的防御机制面前更胜一筹。生物学家雷德尔指出:“来自生态环境的压力,例如躲避捕食动物、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都需要人类祖先做出决策。我认为这些因素在人类大脑的发展进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一些研究人员采用了其他方式来衡量人类社交圈子的规模,他们得出的结果有别于邓巴数字。人类学家拉塞尔·伯纳德(Russell Bernard)与网络科学家彼得·基尔沃斯(Peter Killworth)进行的系列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人数的均值为291人。另一篇发表于《美国统计协会期刊》的论文给出的数字是611人。在社交网络开发者中,也有人将邓巴数字视为一种障碍。当莫林还在Facebook工作时,他曾与公司创始人之一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探讨过行为科学。2008年,莫斯科维茨与程序员贾斯汀·罗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另立门户,成立了Asana公司。这家公司提供的任务管理软件旨在改善团队合作。Path将自身置于邓巴所描述的社交边界之内,而Asana则在寻求突破。
在莫斯科维茨和罗森斯坦看来,Asana或Facebook这样的工具就好比一架望远镜。这是一项可以扩展人类能力范围的技术。莫斯科维茨说:“这样的工具可以令我们更好地追踪这些关系,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了解他们的长处与缺点,而无须进行一系列面对面的交流。”罗森斯坦补充说:“当然,我们还有一项半公开的小任务:扩大邓巴数字。”
如今,Facebook依然时常提及邓巴理论。社会学家、Facebook数据科学团队负责人卡梅伦·马尔洛(Cameron Marlow)说:“我们确实会谈到邓巴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数据时,它堪称是一个有力的框架。”
邓巴已经习惯了针对其研究成果的批评,而且他也做出了回应。邓巴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有能支持他观点的数字。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显示,Twitter用户经常进行互动的好友人数平均在100到200人之间。虽然Facebook允许用户拥有多达5000名好友,但一般用户的好友人数为190人。虽然这个数字高于150人,但邓巴认为这属于误差范围之内。
邓巴没有一个Facebook好友。虽然当妻子在家上Facebook时,他偶尔会瞄上两眼,但他自己没有Facebook账户。按照邓巴的说法,他“误打误撞地”拥有了一个LinkedIn账户。他开设了一个Path账户,但从没用过。
邓巴并不排除人类在社交生活中重新设定认知上限的可能性——人类已经做到过这一点。邓巴指出,与其他灵长目近亲相比,人类之所以能应付规模大得多的社交圈,原因在于数万年前人类发明了语言。狒狒通过轮流抓虱子的方式来巩固感情,而人类用修辞、八卦、演说、唱歌、讲故事和开玩笑等方式聚到一起。邓巴说,正是语言使得人类大脑的处理能力扩大到了150人。在他看来,除非有像语言那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物出现,否则我们的社交能力仍将保持在150人。
撰文/Drake Bennett
摄影/Finn Taylor
编辑/刘坤
翻译/小凡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