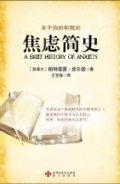第二章 兒童的信任和恐懼
睡吧,你這頭黑眼睛的豬
掉進滿是魔鬼的深坑
——19世紀初,冰島搖籃曲
“哦,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的。”我答道,隨手拉上窗簾。不過,我的女兒克拉拉不是電影裏演的那種孩子,只要哄一哄或輕輕的一個吻,就能很快進入甜美的夢鄉;她從來沒有愉快地入睡過。女兒同小時候的我一樣,是個容易擔憂的孩子。從出生開始,她就極易受到驚嚇,很難安定下來。在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別說是啜泣和急性腹痛了,就連錄音帶發出的噪音也會令她坐立難安。她不會,也無力輕易地消除疑慮。她正是哈佛兒童心理學家傑羅姆·卡根所稱的“高度反應、敏感性格”的典型例子。
“小女孩被綁架離家以後,會死在樹林裏嗎?”克拉拉一再問道,非要將這種可能性打探個水落石出。在我們居住的城市裏,曾經有個大約十歲的黑眼睛女孩突然失蹤了,據說這女孩是在自家床上被綁架的,事件在學校不脛而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人在自行車道邊的溝裏發現了她的屍體。她家的一個熟人被控為謀殺犯。
我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曾是報導犯罪新聞的記者,輕而易舉地就能想像出類似的可怕場景:夜黑風高,憑藉遠處的光亮,一個陌生人順著梯子潛入我家位於多倫多郊區的狹窄後院,並撬開克拉拉臥室堅實的窗戶。不過,我知道女兒感興趣的並不是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她想知道的其實是該如何應對。她清楚至少有人曾經被劫持了,這種事就有可能會再次上演。
克拉拉的大腦正處在發育階段。在她的腦葉裏,杏仁狀的腦下垂體是哺乳動物產生恐懼的感覺中樞,能夠發出五種警報信號。一旦她不能對威脅進行合理的評估,將此信號傳回腦下垂體,就會導致“錯誤的預警”。
在晚上,她出於與白天同樣的原因而感到害怕,一個星期裏就為此哭過好幾回,感到無能為力。歐洲的研究人員最近證實:父母向來低估了孩子恐懼感的強度。(我對此並不驚訝)對靈長目動物以及人類來說,黑暗會加強恐懼的反射。按照神經病學的觀點,在日落後我們的神經波動性更大,也更警覺。與此對比,齧齒動物和兔子在白天則更為機警。
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化裏,我們會讓尚未能抵禦孤獨感的孩子獨自睡在自己的床上。實際上,我們是在要求非常脆弱的家庭成員獨自照料自己。我們讓他們在篝火周邊巡邏,卻不給出任何可沿循的指示;不光如此,我們還不准許他們拉響警報,因為這樣會擾醒我們的安夢。
“當成年人極力回想小時候害怕的事情,”段義孚①在他那本文筆優美的著作《恐懼的景觀》寫道,“他們其實忘了童年的種種快樂,只對茫茫黑夜裏自己的瑟瑟發抖記憶猶新。”
我對黑夜的恐懼記憶猶新。1971年,我跟隨父母住在新德里,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了戰爭(那場戰爭決定了孟加拉共和國的誕生)。當時還有兩個星期就是耶誕節了,而新德里北方較遠的城市還在遭受巴基斯坦軍方的狂轟亂炸。印度首都的所有家庭都接到當局的通知,要將窗子漆成黑色或乾脆封上,以免讓城市暴露在巴基斯坦空軍的炮火下。當時我只是個七歲的孩子,只記得父母之間扼要的談話以及持續而可怖的黑暗。有時候,我會跪在床邊冰涼的石棉瓦地上,祈禱我們的住處不要被飛機夷為平地;真希望房間四周的牆永遠不變,我永遠不要跟所愛的人們分開。因為所有這一切,都可能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變得面目全非。
整個印巴戰爭期間,我們家只發生過一次意外,就是被喚作“蜀葵”的小白兔死了。那是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我十多歲的姐姐本來準備上床睡覺,卻一不小心將兔子踢進茅坑裏。“我想它肯定淹死了。”她解釋道,語氣中充滿愧疚。
① Yi-Fu Tuan(1930- ),當代華裔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他將人的主觀性情與客觀地理的關係進行了獨到的闡發,產生了重大影響。
住在印度的三年裏,我的體重銳減,成了焦慮型厭食者,不敢吃牛肉。醫生開了食療藥方,讓我每天喝香草奶昔,媽媽為此還特地跑到美軍海外軍事基地去購買。那裏有專為美國外交官和軍事人員提供服務的雜貨店。在那裏,“卡夫晚餐”乾酪、“傑米瑪阿姨”早餐,還有炸薯條……在這片異國土地上,看見這麼多美食擺滿了一個個櫥櫃,真是令人安慰。每天下午,我都與一個臉色蒼白的孩子牽著手,從美國國際學校步行回家,書包裏裝著我的史努比午餐盒。我們這兩個十來歲的孩子要避開隨時出現在路上的猴子、橫衝直撞的自行車、摩托車,滿大街散步的牛,到處都是乞丐……這真是讓人感到痛苦和擔憂的世界。我們一直走到那滿是塵土的家門前,才揮手道別。我走進有空調的房子裏,盤著腿在地板上喝完香草奶昔,然後寫寫東西或觀看方形電視機裏播放的寶萊塢電影。
印度是我個人記憶中“恐懼景觀①”的發源地。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描繪一幅獨一無二的心理風景畫。對於那些童年時代就害怕的事物,始終都會保持特異反應般的警覺。心理學家將這些反應稱為“暗示性恐懼”。兒童之所以怕水,是因為曾遇到突發事故,或是其父母過於神經質的緣故。暗示著恐懼的事物還有:狗、沙漠、漆黑的小巷。在街上橫衝直撞的摩托車、遍地的牛糞、無休止的暴力衝突,害怕走失或擔憂被拋棄——我的父母在世界各地漂泊,身為他們最小的孩子,我心裏總是缺乏安全感。
① 段義孚所提出的概念,他將人們的感受與環境景觀聯繫起來,提出有脅迫性的環境是恐懼的來源之一。
我對大型肉食動物的感知,是從八歲那年的夏天開始的。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公署的司機桑尼興高采烈地開車載著我們,從新德里北部出發,前往舊英國驛站,它位於喜馬拉雅山東邊山腳的比姆塔爾。那是一個毗鄰冰湖的高山溪穀,就在科貝特國家公園附近,是印度著名的食人虎的棲息地。我們在一幢房舍安頓下來,屋主是一個叫斯梅塔塞克的捷克人。斯梅塔塞克先生熱愛探險,他擁有大批神秘的收藏品,比如用大頭針釘住的、稀奇古怪的蝴蝶標本。
這次旅行讓大人們平日裏的緊張情緒得到紓解,三個十來歲的孩子則情緒高亢,我也一樣。我坐在紅色的旅行車後座,順著後窗向外眺望,環繞德里灰濛濛的平原上儘是坑窪不平的泥路,婦女的背上好像馱了很多草,走起路來十分艱難。直到我們的旅行車開上滾燙的柏油路之後,她們那背部高聳的奇怪模樣仍久久留在我的腦海裏。經過幾小時的顛簸,大家在孩子們的吵鬧聲中到達山麓,蜿蜒向上爬坡數千英尺後才抵達比姆塔爾。
在這次全家旅行的途中,不知道是什麼事觸怒了媽媽。也許是因為桑尼錯過了彎道、迷了路,或是爸爸發了脾氣,反正當時車上亂哄哄的,就在大家都嚷嚷著“見鬼去吧,全都見鬼去吧”的時候,向來性格沉著的媽媽突然要求下車。她沒特別想什麼,“只是……那輛車有點讓人緊張,我受不了。”她後來回憶。由於一心想要逃離,她使勁抱著我,把我像圍巾似的繞在脖子上,就這樣下了車。旅行車的尾燈像老虎的眼睛一樣在前方閃爍,直到離開我們的視線。我們開始步行,去哪兒?“我想只有幾步遠,”她對我坦承道,“也許要走一百多米吧。”
在那個可怕的漆黑夜裏,月亮藏在厚厚的雲裏,只能隱約見到數百英里外城市上空的光亮。沒有可以照亮道路的手電筒,我們只好試探著艱難跋涉。當時是雨季將至的七月,每年這個時候,農民會在山坡點燃雜草,驅逐鬼怪。遠方若隱若現的橘紅色火苗,顯得眼前的黑暗愈發深不可測。
那是《韓塞爾與葛雷特》①裏面的場景,仿佛電影《魔戒》中的弗羅多和薩姆也曾在這裏出現過。在某種神秘感的驅使下,我們一步步向前走。“我們下方和上方的整座小山丘都有火光。”媽媽說。最後,我們終於在旅社找到了其他家人,他們正擔心得焦急難耐。斯梅塔塞克先生告訴他們,山上的獅子每到夜晚就在這個地區尋覓獵物。在令人心驚肉跳的寂靜中,我們收拾好行李,各自上床睡覺。我對這次度假旅行零零散散的記憶中,還殘留著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不得不去應對的危險徵兆。
我還記得當年我是如何扶著一道低矮石牆,想像自己是芭蕾舞者,盡力保持身體平衡卻還是搖搖晃晃,豎起耳朵聆聽著灌木叢發出的沙沙響聲。就像一頭鹿,表面平和,保持高度的警惕。
①《Hansel and Gretel》,格林童話所收錄的德國童話,中譯本名為《糖果屋歷險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