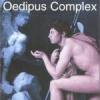引言: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并未从精神分析理论体系资源中系统地阐述俄狄浦斯情结,但他却将其视为神经症患者的“核心”情结,并同时在《图腾与文明》一书中将其泛化成所有人类文明所普遍存在的内心结构。可见,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氏理论的体系中占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并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界、文化人类学界不同视角的解构与重构,颇值得玩味。
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被视为儿童在性蕾期(3-5岁)间所感到的对双亲的爱恋与敌意并存的冲突组织。在此阶段,儿童的自我功能通过中立化过程相对以前的阶段得到更多的发展和整合,表现在儿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稳定的客体关系,个体感受到的焦虑从害怕“客体的丧失”发展成害怕“客体的爱的丧失”,因此,当个体发现还有第三人占有着所爱的客体时,儿童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改变:羡慕、谋杀和乱伦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深的恐惧让儿童的内心充满冲突。儿童为避免这种恐惧或焦虑过于强烈,不得不认同这些欲望中的客体——父母,并像父母一样拒绝这种欲望,超我在这种对父母道德的认同中形成了。一旦内化的超我形成,便随时随地对本我(即儿童以性欲方式占有客体的利比多)起着监督和控制的作用,而这种监控则是通过对自我的支配实现——一方面帮助自我建立防御机制,另一方面则使自我失去行动的自由,通常表现为症状。这种模式延伸到儿童内心世界即表现为个体、所爱的客体、竞争对手或执法者(多指具有权威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并投射到个体外在环境中复杂的人际情感关系,这种时刻的冲突就成为个体一生人际关系的基模。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框架中,俄狄浦斯情结在人格的结构化与左右人类的欲望上扮演着根本角色。
文化人类学曾试图寻找证明俄狄浦斯情结非普世化的依据,比如说在具有母系特征的原生态文明部落中发现并不存在阉割焦虑,但另一部分学者依然发现即便在这样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个替代父亲权威的执法者角色。无论如何,就俄狄浦斯情结自身而言,其存在应具有三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特征:1、具有惩罚性特征的超我的存在;2、并非源自本能的焦虑,而是具有一种冲突性的罪恶感、内疚感的“高级”情绪特征;3、存在着三角关系。这三个特征同样体现于客体关系学派的视角中。
一、克莱因的俄狄浦斯情景(Oedipus situation)
克莱因提出的偏执-类分裂位状态位于生命头四个月,此时婴儿所面临的生理和心理任务几乎完全一致,并且是未分化的,即尽可能的保存“自我”,这里“自我”的含义不仅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功能性含义,而是混合了躯体和“具有一些凝聚与整合的基质”,这就是被克莱因称为生本能的体现。自然,在此阶段,任何外界环境的挫折加之内在的死本能的运作都会激发并被婴儿体验为巨大的迫害焦虑,此时的焦虑类型本质上属于对自身的死亡焦虑,表现为被迫害-攻击、施虐-受虐的特征。婴儿为应付如此巨大、高强度的焦虑,使用内摄、分裂、投射的防御机制,将乳房分裂为能满足自己口腔原欲的好乳房和无法满足的坏乳房,并且内摄好乳房,投射坏乳房,进而通过内摄-投射互动过程逐渐内化成好客体和坏客体,尽管此时婴儿无法整合这些部分客体,但一个重要意义是它们形成了早期的超我。
婴儿进入抑郁位状态的前提是在内摄-投射好客体的互动过程中,作为生本能的体现的爱的利比多压倒代表死本能的破坏冲动,进而逐渐增强了自我功能,使得婴儿逐渐能将部分客体整合为完整客体,即婴儿会觉得好乳房和坏乳房原来是一体的。此时,最初的罪恶感和内疚感出现了。婴儿会体验到原先想撕咬、毁灭、控制的坏乳房原来正是那个带给自己愉悦、满足和爱的感觉的好乳房,这种矛盾打击了理想化和全能感,从而产生了一个具有类似于范式转移的变迁——婴儿依然担心自身的毁灭,依然有强烈的迫害焦虑,但在此之外,婴儿开始担心(完整)客体的丧失,即婴儿担心自己的攻击冲动毁灭那个带给自己爱与温暖的好客体,同时,随着自我功能的增强,迫害焦虑变得逐渐能忍受。
至此,俄狄浦斯情景的冲突已然产生,三位主角分别是自我、好客体、坏客体,一方面,婴儿将完整的好客体再度分裂成两个内在客体,健康的好客体和濒死的坏客体,婴儿体验到的罪恶感驱使其试图修复它,但此时,婴儿的自我感到具有迫害性的坏客体(被投射出去再内摄而形成的超我的化身)依然无时无刻不威胁着好客体,进而使用了否定与全能的躁症机制来对抗愧疚、绝望及被消灭掉的感受。尽管如此,由于抑郁位的婴儿原欲的表现形式依然以口腔或肛门为主,附着在性器上的利比多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因此,婴儿超我,即内化的迫害客体,是以一种“有阴茎的女性”的古怪客体形象出现。
克莱因的俄狄浦斯情景的意义在于婴儿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容器以及客体关系,为婴儿可以和母亲之外的第三人建立关系奠定了基础。其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自我的去中心化或去整合化,这样导致的后果是(被)迫害焦虑无法被自我容纳,带有攻击性和吞噬性的嫉妒无法转化为抑郁位的羡慕,以致被迫退行到偏执-类分裂位。
实证主义心理学提供的依恋理论为这一期间的俄狄浦斯情景提供了一个非常契合的例子,即6—7个月大的婴儿出现陌生人焦虑的现象,从依恋理论上说明婴儿的母婴依恋开始建立,从客体关系层面上说,是早期俄狄浦斯状态的外显化,即自我、母亲(爱与依恋的客体)与陌生人(客体的丧失、迫害焦虑的残余衍生物)之间的三角关系。
二、费尔贝恩的俄狄浦斯情结
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模型取消了弗氏理论中本我的概念,修改并增强了自我的概念及功能,同时亦使得超我的涵义发生了变化。
费尔贝恩的内在心理结构的核心是中心自我,亦即和客体发生关联的原初动力性结构,并因挫折进入到一种分裂状态:挫折意味着关系的切断或阻碍,当挫折发生时,婴儿将感受到的混乱体验分裂成“中心自我—理想化客体”的核心结构以及另一个难以承受的情绪体验部分,此一部分随即被潜抑至无意识层面并继续被分裂为两种亚结构,一种是那些被逐出中心自我而急于需要满足且具有强烈需求动力的自我与那些一直在引诱的部分配对成“利比多自我—兴奋客体”亚结构,另一种是拒斥性的、挫败性的面向以及与之衍生出的具有愤怒、攻击性的自我配对成“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亚结构,由于每一种亚结构均具有能量,并能独自运作,因此“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单元则会对“利比多自我—兴奋客体”单元进行继发的潜抑。
“反利比多自我—拒斥客体”亚结构实际上扮演了超我的角色,恰是因为婴儿无法适应或接受一个危险的、真实的外部环境,而不得不内摄将其转变成内在可控的心理环境,为保住外在环境的安全感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内在的冲突和焦虑。在此过程中,反利比多自我扮演了一个惩罚性的“内部破坏者”。
当婴儿进入过渡阶段时,分裂状态已然形成,此时婴儿开始摆脱依赖阶段的原初认同,不再天真地认为“其他人的就是我的”,逐渐体验到自己和他人的分离,此时婴儿的无助感和冲突显现,这是费尔贝恩的俄狄浦斯情结形成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同时,婴儿将分裂的内在亚结构投射到与之联系的外在客体上,通常是父母双方,由此,便形成了自我、拒斥性客体(通常是父亲)、兴奋性客体(通常是母亲)的三角关系。
费尔贝恩对俄狄浦斯的解释不但能使人容易理解儿童对异性父母的既爱又恨的冲突,同样亦能很合逻辑地解释儿童对同性父母的爱恨冲突,进而解释了个体成年之后的性取向问题——只要兴奋客体投射至同性父母,而拒斥客体投射至异性父母,这一点在克莱因的概念中和“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应。从这个角度讲,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说对于俄狄浦斯具有更弹性并更易理解的解读空间。
小结A:
客体关系学派对俄狄浦斯的理解剥离了经典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情结的三方主体性,并将其还原为个体生命早期内在体验的分裂与整合,因此使该概念实际上具有无可辨驳的普世性。可以这么说,只要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爱恨情仇,只要我们还能体验到时而狂乱时而温柔却又难以自持的情绪,只要婴儿依然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成长,那么我们就始终无法否认其存在的意义。围绕着俄狄浦斯产生的概念从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还应是人类在自身进化史上留下的里程碑。人类走出森林才认识到自己的狭隘,而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就已经体验他者的存在,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当我们从混沌走向两极,再从两极熔炼出三的真味时,或许我们能明白:一分为三,道之所存。
小结B:
我一直觉得“1+1=3”这事很有趣。爸爸妈妈在一起可以生出小孩,但这第三者和前两个原本相称互补的对象来说太不同了。
“黄马骊牛三”(公孙龙),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就是“数婴儿、数母亲,则婴儿、母亲二;数婴儿母亲,则婴儿母亲一。”——根本没有婴儿、也没有母亲这回事嘛!
或许三是在强调作为系统的整体性。如果只是提及对立两极之间的中介,人的生命轨迹就好像被限制成了一条线,就好像一个粒子,在“好客体”、“坏客体”或者
“拒斥性客体”、“挑逗性客体”之间犹犹豫豫地徘徊。而一个单独的自我,使我眼前出现一只弹弓,弹弓的皮筋或许松弛、或许绷紧,也许会有一颗石子在上面朝着谁家的玻璃蓄势待发。
一个圆圈中间被一条曲线分成黑白两半之后,它还是一个圆圈。或者你可以管它叫O。如同一个椭圆,那椭圆的形状来自一个变动点的轨迹,它到另外两个固定点之间距离的和是一个固定值。此消彼长,如同家庭中的爱恨均衡。
“0、1、10”也有趣。这种方法名为二进制,但是2在哪里?
超越也许意味着变形,也许意味着无法用原有系统描述,也许意味着对原有系统的全包含,也许还意味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据说在超越位对O的体验是这样的:它看起来似乎会永恒地抑郁,又带有ps位的焦虑和beta元素。(Grotstein,1997)
当人超越的时候,上帝就没有了,被人取代。怹将怹爹娘赶出伊甸园之事也一并消失了。
这令我想到里尔克的一首诗——《孤寂》
孤寂好似一场雨。
它迎着黄昏,从海上升起;
它从遥远偏僻的旷野飘来,
飘向它长久栖息的天空,
从天空才降临到城里。
孤寂的雨下个不停,
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
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
失望悲哀,各奔东西;
当彼此仇恨的人们
不得不睡在一起:
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