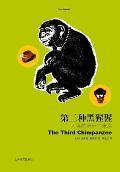序言
究天人之际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最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