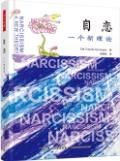前言
James S. Grostein
在本书中Neville Symington讨论了我们常常会碰到的自恋这个主题。他从与罹患这种障碍的病人长期的临床工作经验中提炼出了新鲜的洞见。他所采用的视角非同寻常并给人以启迪。他不仅从克莱因的本能夸大/躁狂防御的立场,以及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巴林特和科胡特的创伤-缺陷概念这些众所周知的方面理解自恋这个主题,还从深刻的本体论的不安全性这个独特的角度。尽管他受训于英国独立学派且是其中的资深成员,但他探讨这个障碍的角度是从我们今天称之为离开(departure)的存在主义观点。婴儿/儿童做了一个无意识的选择,要么是朝向生命给予者(它的真实性或自发性),要么是否认它,并用魔术性的伪装来逃避心理的真实以及回避外界的现实,后者成为了自恋性障碍。
我理解的生命给予者是一个内在、幻影、像过渡性的客体,它由自体的不同侧面以及外在生命的支持性客体组成。根据Eigen的说法它是一个客体,人格化了比昂、拉康和温尼科特所描述的“信念的行动”。部分地抛弃了生命给予者后,不幸的自恋主体被分割成解离的亚-自体或他我(alter ego)。它们彼此冲突,反抗整合,丧失了作为首创者的自发中心的感觉。
以上是作者主题的一个骨架性的概要。首先,我要概述一下历史上对自恋这个概念进行的重要阐述,以帮助确认Symington显著的贡献。在精神分析持续的历史性转化的长河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它在一系列的辩证(dialectic)中流动的倾向。先是优先选择一个概念,然后是另外一个,接着就是一个短暂的和解的综合;接下来又是另外一系列的辩证,每个系列都构成了两元相对的结构。自恋概念的发展历史很大程度地受到这个辩证过程的影响,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展示出来。精神分析源于无意识创伤记忆和意识(其中无意识由稽查制度所创造出来)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很快演变为无意识系统和意识系统间的冲突;在后面这个范畴下滋生了力比多和潜抑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后又是力比多本能和自我本能间的辩证关系。
弗洛伊德有关自恋的那些发现使其抛弃了这个辩证过程(1914c)。与此同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元心理学的论文上。然而在论文中,他对自恋的概念是:(1)出现于自体性欲之后,但是在选择情感依附的客体前的一个阶段;(2)原始的自恋是无客体联结的状态;(3)继发性自恋预测着自我从与客体相联结撤回,其目的是再次就位于原始的自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继发性自恋的状态构成了自恋类型的客体关系模式。当“客体的阴影落到了自我上面”,这个阴影的阴影(认同)将再一次轮流落在外部世界的客体上—也就是说,外部的客体会以他们好像是自体的一部分的方式被对待。
在自恋这个概念的发展史上,下一步是它被视为抑郁症者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哀悼和抑郁》一文(1917e〔1915〕)是弗洛伊德对客体关系理论的最深刻的贡献,而且成为梅兰妮·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贡献的模板和起源。此外,通过提出自恋和客体关系间的辩证关系,它继续了一些在《关于自恋:一个介绍》中没有被回答的主题。在《哀悼和抑郁》中,弗洛伊德介绍了他的发现:当个体无法忍受客体(实际上行使着部分客体的功能)的丧失时,个体有能力通过内化丧失的客体,从而在无意识幻想中否认这个丧失。此外,客体被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客体,一个被分配给与自我理想认同了的关系,作为“自我中的梯度”(as a gradient in the ego);而另外一个与自我本身认同。弗洛伊德接着继续说,前面的结构采用了最大化的施虐来对待后者,后者维持了与它的受虐性的关系。丧失的部分被成功地否认了,然而其代价是内在的抑郁(迫害)。因此,这四个实体(两个部分客体和两个部分自我)的互动构成了继发性自恋的状态,而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内化的自恋客体关系。
分裂以及随后的自我和客体分配使得可以把抑郁症动力性理解为由两个、而实际上是四个内在结构的施虐受虐关系构成。这些结构也构成了客体关系和自恋间的辩证关系。克莱因(1940)从这个内在的动力结构中发展了她的理论:偏执-分裂位点的(“前-抑郁”)迫害性焦虑和抑郁位点的抑郁性焦虑;而费尔贝恩(1940)把弗洛伊德的自恋-抑郁范式视为分裂样状态的证据,从中他详细描述了他的“灵魂中的结构”的六个成分。
从另一角度讲,弗洛伊德开拓了很多我们对自恋和客体关系概念的理解,但他从未充分地澄清作为客体关系和作为非客体关系(原始自恋)的自恋间的区别。当我们回溯时,他的精神病的概念,其实是自恋性神经症—也就是说,对客体的投注被撤回到自体中,因此客体关系不再存在。正因为此,他假定自恋性神经症与心理神经症不同,是无法被分析的。这一论点使得精神分析纷扰困惑,并要为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和正统/传统学派之间的大论战负部分责任。英国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寻求客体的;而正统/传统学派认为婴儿是不会寻求客体的,它处在孤独-自恋的膜中,在它被“孵化”之前是不会寻求客体的。然而贯穿整个论战,其争执都在于客体相对于驱力的重要性。尽管大家用了种种派生的形式来对自恋进行描述,特别是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自恋依然处在昏暗不明的状态中。
在这背景中还有另外一对辩证关系,而这一对在随后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即自我缺陷论和心理冲突论,选择缺陷理论的人有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巴林特、鲍比、沙利文和科胡特;而克莱因落单地与自我心理学联盟,维持了把冲突理论放在第一位。
在英国客体关系运动的早期,可以观察到精神分析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支的辩证关系。其中一方是克莱因,另一方是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他们分别研究着“客体关系”,最终把首先由弗洛伊德发展出来的自恋理论向前推动了一步,将其呈现得更为清晰。对克莱因来说,自恋(她极少用这个术语,也没有正式地谈论过这个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对客体的永恒的内在幻想,婴儿内射性地认同了这些客体,这揭示了婴儿如何通过初始的分裂样和躁狂防御转化了对客体的感知。换言之,根据克莱因的观点,婴儿是而且变成了他所认为曾经对客体并还在对客体所做的那些事—以及他如何防御这些觉知(躁狂性的防御)。这个假设是基于这样的概念:被公认的意图性或意志的主体性根源(投射性认同)。这一点是Symington所强调的—我相信他的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对的。其他的理论家—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甚至是科胡特—对无意识意图的论述是不足的,而且看起来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创伤-缺陷理论:无助的婴儿和客体提供的不利环境间非辩证性的关系。因此,克莱因似乎成了为外部客体(主要是乳房)而工作的调查员,她假定婴儿在滥用乳房,并对此进行调查;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通过在所推断的意图和心理幻想间建立联系(主要是投射性认同),她肯定了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关于自恋性客体关系的直觉。在她手上,弗洛伊德(1917e〔1915〕)和亚伯拉罕(1924)对自恋者(无法哀悼,只能随着客体一起丧失或者完全否认丧失本身)内心世界作为相对静止实体的描述变成动态的、活生生的了。
另一方面,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以及巴林特、鲍比、沙利文、科胡特等人)成了为婴儿而工作的调查员。但最后是科胡特(1971)提出把对婴儿的调查员职责看作“自体独立的发展线”(独立于客体关系,如俄底浦斯期和情结)。科胡特创新性的权威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贡献,后来在美国成了一个真正的宣言。就如同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女性意识的时代,在婴儿发展和儿童虐待研究的帮助下,科胡特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解放了婴儿和儿童。“正常自恋”和正常的自恋性权利的时代到来了。简单地说,婴儿和儿童有权利要求、他们的父母也有义务和责任提供最低限量的“自体客体”需求:安慰、镜映、监督、协调一致以及可以理想化的陪伴(“孪生”),以允许婴儿/儿童发展自体凝聚感。
距今不久,自恋这个概念因为与边缘性障碍的比较而复兴,边缘性障碍构成了一些更为常见的原始的心理障碍。罗森菲尔德(1987)重申了客体关系(弗洛伊德间接提到这个概念,但矛盾的是,他又反驳了它)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再次援引了弗洛伊德早些时候对自恋中自我理想的重要性的强调,并构想了一个特征性的内在客体—一个空想的蒙太奇或者魔鬼。可以这么说—那是由自我、自我理想,以及“疯狂的全能自体”构成的。当它在临床情境中起作用时,罗森菲尔德冠之以术语“自恋性的全能客体关系。”后来科恩伯格(1984)借用了罗森菲尔德的意象,并构造了他自己的“魔鬼”,这个魔鬼的特征是有着“病理性的夸大自体”,并由以下三者构成:(1)真实自体、(2)理想自体、(3)理想的客体呈像。
在自恋的历史上,还有一个方面需要讨论—也就是自恋与癔症的神秘关系。癔症这个神经症统治了19世纪的精神医学并成为精神分析的源起之处,但在这个世纪的后半页变得衰退了,让位给了当前兴起并很普遍的人格障碍—一种温和的冷漠、 “隧道视野”,情感处于表面的性质、在客体关系中肤浅和操控性的性质,这些都特征性地描述了Symington脑海中的人格特质,特别是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托尔斯泰小说中悲剧性的女主人公。
现在Symington提供了另外一种辩证关系—在选择或者坚决放弃生命给予者之间。对于前者,一个人会获得健康的心理基础;对于后者,就变成了病理性的自恋。作者核心的插入点似乎是,健康的心智和病理性自恋间的平衡在于自恋性损害的创伤在婴儿期被处理的方式—究竟婴儿是屈服于它们并变成了一个内在的恶毒的破坏者的囚犯(费尔贝恩的阴影),或者他选择了抓住生命的礼物(人格化了生命给予者),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在此我们会想起很多的作者,其中有克莱因和她的追随者,他们那么辛苦地聚焦于分离的主题以及“缺口”,还有Eigen(1981),如之前所提及的,以及他对温尼科特、拉康和比昂所提的“信念领域”的贡献。
我自己曾经独立地探索过这个主题,它在婴儿发展和精神分析技术中处于十分核心位置,我的方法是援引心理学中的单纯(innocence)和丧失单纯。克莱因、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同意,婴儿似乎在面对迫害(克莱因)和/或者创伤(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时,会分裂他的客体和他的自我。克莱因强调了抑郁和前抑郁(迫害性)的方面,费尔贝恩强调的是这个分裂的分裂样性质,而温尼科特做了“真实和虚假自体”的表述。换言之,从单纯的角度,可以说弗洛伊德和克莱因把本能驱动的婴儿视为潜在的不真诚,因此也不单纯,但是有能力建立单纯,这是俄底浦斯情结(弗洛伊德)成功修通的结果,以及/或者是达到或超越到抑郁位置的结果。可以认为,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和科胡特的观点是,严峻的创伤和剥夺会使得原本单纯的孩子失去他的单纯并且继发性地变得不真诚。温尼科特(1956)在他的《反社会倾向》中强调了丧失单纯。
首先让我们注意到原始的单纯这个概念及其命运的,是William Blake(1789—1794)的《单纯和经验之歌》。在书中,他提出婴儿拥有原始的单纯,但这份单纯受到“经验的森林”(生活)的考验,如果他成功了并保持不妥协,他就超越到一个更高的单纯中。与单纯相联结的是与一个客体的联结,其本质相当于一个盟约,而丧失单纯的后果是一个未履约的状态,在其中个体觉得受到浮士德式交易的束缚(浮士德式交易:为换取权力、知识或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精神上得不到满足而苦恼—译者注)(Blomfield,1985),甚或是恶魔般的内在客体的束缚,总是体验到受到那个客体的意图或意志的影响或操控,非常像Tausk(1919)的“影响的机器”的早期阶段。个体失去了他的自发性—这一点是Symington具有创新性的贡献,就如同阿里阿德涅帮助情人走出迷宫的线一样。
Symington断言自恋者通过对创伤的回应做了选择,他的概念—接受或者拒绝“生命给予者”,跨越并整合了冲突-缺陷两派的争论。这一论述,阐明了作者的信念,同时作者也听取了创伤-缺陷流派的观点,即自恋性障碍总是起源于创伤情境,但是,是个体对创伤的回应决定了究竟是产生自恋性的弃权或者丧失单纯,还是产生真实的自体。
通过引用Frances Tustin的著作,作者还搭建了另外一个概念性的桥梁—孤独症和自恋之间的桥梁。我们已经看到,克莱因构建的自恋在本质上是躁狂,而费尔贝恩认为自恋是分裂样的。Tustin对孤独症障碍的引人注目的研究帮助我们应用她的一些概念到自恋者中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同孤独症孩子,自恋者使用客体并不是以正常的分享关系来获得正常的依赖和相互依赖,而是一种操纵性、寄生性的关系,在其中客体被诱惑并被控制,以此来使得自恋/孤独症主体保持全能和保护性的外壳。如同孤独症的孩子,自恋者憎恨客体关系,但又黏附于关系中,因此要操控他们来满足病理性的需求—也不得不受苦于其后果。他们憎恨独自一人,憎恨自己需要客体,但他们否认自己忌妒的情感—通过在幻想中盗取他们所需要的客体的那些品质来回避忌妒和感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是如此的未整合时,他们永远无法逃脱深刻的羞耻感。
Symington的概念—生命给予者在正常和不正常的自恋中建构了独特且整合的观点,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