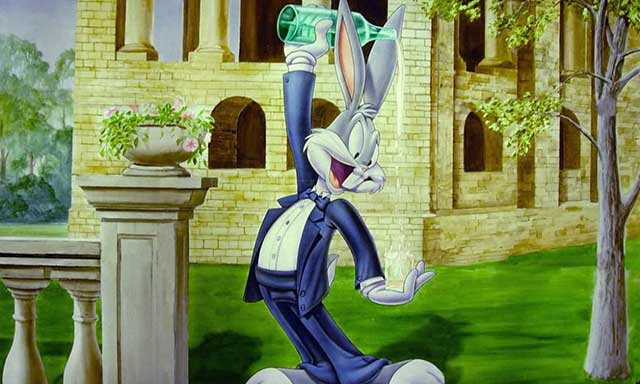
在接收到往特定方向记忆的要求时,千万要特别小心。从压力中脱身,尽可能在自由的状态下去回想,才能防止虚假记忆发生。特别是,如果突然想起了之前想不太起来的记忆,就要怀疑那是不是虚假记忆。
我不记得去年夏天做过的事……
记忆中的某件事栩栩如生,细部内容记得很清楚,连记忆出自哪裡都十分确信,愈是如此,愈容易相信自己的记忆为事实。但是根据虚假记忆的研究,就算满足了上述所有条件,自己记得的东西也有可能不是真的。
定义: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件,却认为曾经发生,并从记忆中撷取的现象。也就是说并不是实际的记忆,只是相信自己记得的错觉。
一九九〇年代,童年时期的记忆问题在法律诉讼上受到关注,造成虚假记忆的研究开始蓬勃。一九八〇年代与一九九〇年代向心理医生求助的女性中,有许多人表示困扰自己的心理问题根源,来自于年幼时期被父母或亲戚性侵的记忆,极为生动且详细的记忆,使她们的情绪大受衝击而告发加害者。恢复记忆与治癒相关的书籍进入畅销排行榜,影响所及,发现童年时期创伤的人们,纷纷提出诉讼。甚至不只童年记忆,连前世治疗——挖掘上辈子的记忆,试图寻找心理安定——都引发人气。
但在寻找心理治疗师之前,一次都不曾想起的记忆,为什麽会涌现呢?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教授,数十年间的研究结果,人类的记忆相当不可靠。她认为心理治疗师在推动「恢复被压抑的记忆」过程中,引发複杂的社会问题,有必要提出正确的科学解决办法,因此投身研究相关问题。
一九九三年,洛夫特斯教授进行了简单的实验。她首先让受试者阅读以童年时期的三项记忆编写的小册子。童年时期的记忆事先由受试者的家人提供,但裡面有两个真正记忆(童年时期实际遭遇的事件)与一个假记忆(在购物中心迷路的记忆)混在一起。之后,洛夫特斯教授请受试者详细写下自己记得的内容,不记得的就不要写。
从逻辑上来想,受试者应该会写下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不会写下研究团队故意捏造的购物中心迷路记忆才对。
然而在整体受试者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五表示记得自己在购物中心迷路,做出详细描述,并谈起情绪上的衝击,例如「妈妈要我不要再那麽做」、「那天我实在吓坏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家人,我也知道事情很严重啊」、「进到玩具店后迷路了,我左顾右盼,心想事情不好了,好像再也见不到家人一样,真的好可怕。那时有某位穿著蓝色衣服的爷爷走向我,是一位年纪很大的爷爷,头髮花白而且秃了很多,爷爷戴著眼镜」。
生动且详细的描述,加上情绪衝击,很容易就相信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但这都是根据研究团队捏造的假事件,自己再编造出来的记忆,也就是虚假记忆。研究团队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中阅读分发下去的小册子前,这些记忆一次都不曾浮现。就像寻求心理医生协助的女性,想起了生平从来没有想过的性侵记忆一样。洛夫特斯教授没有做任何诱导提问,甚至提醒想不起来的记忆就不必写,但还是出现如此惊人的结果。
不过,如果是心理治疗师的话,会因为要找出被压抑的记忆,所以先丢出与幼年期记忆相关的线索。接受治疗者,如果将电影或新闻报导中看过的儿童性侵画面,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觉得会不会自己也是那样的话,渐渐就会製造出记忆。
洛夫特斯教授在其他研究中,让童年时期曾去过迪士尼乐园的学生看了广告照片,照片中迪士尼乐园裡兔八哥(Bugs Bunny)牵著一个小孩的手。研究团队请那些看过照片的受试者,具体描述童年时期在迪士尼乐园内遇见兔八哥的画面。参加实验的学生中,有百分之六十二记得与兔八哥握手,有百分之四十五记得与兔八哥拥抱。有些学生则记得摸过兔八哥的耳朵或尾巴,甚至还有学生生动地记得,自己给兔八哥胡萝卜。虽然这些学生可能有非常卓越的记忆力,但问题是,兔八哥并不是迪士尼乐园的角色,所以在那裡绝对遇不到他。那张广告照片是假的,实验学生的记忆自然也是假的。
虽然我们总是认为,如果能仔细描述情况(别人或是自己本身),就愈接近事实,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的记忆,并不是被动複製外在环境,然后再「撷取出来」,而是一直主动重组意义,不管要多少生动的记忆都能「做出来」。不只洛夫特斯教授,另有许多认知心理学者说明,记忆的特性不是像蜜蜡一样,一旦複製后就会留有确切的型态,而是像「变化无常的黑板,不断地用粉笔与板擦涂写又擦掉、擦掉又涂写」。
洛夫特斯教授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记忆VS.创忆:寻找迷失的真相》(The Myth of Repressed Memory: False Memorie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一书中,介绍了理所当然的虚假记忆案例,例如威尔科默斯基(Wilkomirski)将幼年时期遭遇的大屠杀经验,传神地呈现在书中,获得讚誉,但事后被揭露所有的记忆都是假的;还有宣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九死一生逃脱出来的故事等等。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九八八年冷血的杀人犯,因为性侵家人、崇拜撒旦,被两个女儿告发的英格拉姆(Paul Ingram)。警察採信女儿被父亲虐待的证词,逮捕了英格拉姆。警方为了让他招认罪行不断审问,他最终屈服了。长久受到审问的他心神虚弱,按照警察的诱导审问,创造了自己的记忆。当然,因为十分朦胧模糊,本人也分不出到底是事实、是梦、是电影,还是新闻报导中的内容。
洛夫特斯教授拜託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可受暗示性)专家,访问英格拉姆。暗示感受性专家向英格拉姆表示,他的儿女对他提起告诉,罪状是强制性侵。英格拉姆一开始否认犯行,但是在暗示感受性专家催促他「你回想看看那个场面」后,隔天他就承认了犯行。
但是,上述告诉内容是假的,是暗示感受性专家杜撰的故事。专家主张,英格拉姆之前的所有自白,都是捏造的虚假记忆,是在诱导审问后创造出记忆,然后才自白的。专家并提出报告,指出不应该以这些记忆为基础判断他有罪。英格拉姆的律师则表示,仔细检视这个事件的话,会发现女儿回忆的杀人案件中,包含事件的相关新闻报导中曾出现的谬误,不仅前后不一致,也有许多内容被重组,问题重重。最后,英格拉姆被无罪释放。
洛夫特斯教授强调,就算只是小小的暗示,也能製造出虚假记忆,所以必须要小心。然而,就算是虚假的记忆,本人也会认为都是事实,并且坚信不移。洛夫特斯教授在实验结束后,告诉受试者他们的这些记忆都是假的,他们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甚至矢口否认。
人们常常受到诱导提问的影响,重组了自己的记忆内容。洛夫特斯教授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间进行的实验中,让受试者看了汽车交通事故的画面,然后以三种问句提问。她向第一组提问:「您刚刚有看到两台汽车开著开著,然后碰一声猛力相撞的影片吧?汽车驾驶的速度大概有多快?」向第二组提问:「您刚刚有看到两台汽车开著开著,然后啪一声撞到的影片吧?汽车驾驶的速度大概有多快?」最后向第三组提问:「您刚刚有看到两台汽车开著开著,然后轻轻擦撞到的影片吧?汽车驾驶的速度大概有多快?」
虽然实验参加者看的是同一部影片,但是回答却根据提问内容而有所不同:第一组受试者回答时速九十公里、第二组回答时速六十五公里、第三组回答时速五十公里。如果再追问:「刚刚红绿灯不是黄色的吗?」即使实际上是亮红灯,受试者也会记得影片中的是黄灯。
在另一个研究中,让受试者看了在空荡荡的街上,有个蒙面男人登场的电影,然后询问:「您记得那个男人的脸上有鬍子吗?」大部分的受试者回答,记得男人的脸上有鬍子,但实际上男子是蒙著面。目击者的证词难以信赖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诱导审问,从假的刺激而自发性地回想的案例中(迪士尼乐园的兔八哥、在购物中心迷路)能观察到的一样,基本上人类有容易产生虚假记忆的认知特性。即使是同样的情况,人们在回溯记忆时,有依据周遭环境、必要性或诱导,而重组记忆的强烈倾向,并且相信重新建构过的记忆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在接收到往特定方向记忆的要求时,千万要特别小心。从压力中脱身,尽可能在自由的状态下去回想,才能防止虚假记忆发生。特别是,如果突然想起了之前想不太起来的记忆,就要怀疑那是不是虚假记忆。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太过依靠自己的记忆,与其他人的记忆做对照,并努力比较客观资料。
本文摘录自台版书《为什麽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不知不觉掉入的101种惯性思考陷阱》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