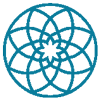摘 要 由于自尊并不能完全地预见个体心理健康的程度, 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构念。本文介绍了其中的努力之一, 在吸收东方佛学思想的基础上, Neff 于2003 年提出了自悯这种新的自我观形式。文章介绍了自悯的成分, 即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感和正念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 然后, 从早期经验、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了自悯的影响来源; 在心理功能方面, 自悯能有效地帮助个体应对负性事件, 增强积极的心理品质和力量, 对人际知觉和互动也有重要影响。自悯的这些积极功能已经在临床上得到了运用。最后, 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自悯; 自尊; 正念; 自我观
分类号 B848; R395
1 引言
怜悯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人类的优秀品质。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恻隐之心”看作人的四善端之一; 在西方, 怜悯也备受赞许, 亚当·斯密把它视为道德的基础。在心理学中, 有研究者(Haidt,2003; Keltner & Goetz, 2007; Singer & Lamm,2009)认为怜悯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遭遇感到关切时所体验到的情绪。怜悯通常由他人的痛苦或悲伤唤起, 并引发助人、安慰或其他减缓他人痛苦的行为。有关怜悯的实证研究表明, 具有怜悯心的个体更可能对他人的痛苦加以关注, 进而在行动上帮助那些状况不佳的人(Eisenberg, 2002)。最近, 脑成像的研究也发现, 怜悯会激活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而这一脑区通常涉及观点采择, 激活程度更高的被试往往施与对手更少的报复性攻击行为(deVignemont & Singer, 2006; Lotze, Veit, Anders, &Birbaumer, 2007)。这表明怜悯可能会激发帮助改善他人福利的动机。不仅如此, Singer 和Steinbeis(2009)论证了怜悯在合作中的作用, 基于怜悯的动机会缓冲背叛的效应, 当被试面临他人的背叛时, 怜悯能够防止合作的破裂。怜悯不止服务于助人、合作等社会功能, 最近的研究显示怜悯对个体的健康具有益处, 它能改善个体的免疫系统和应激反应(Pace, Negi, Adame, Cole, Sivilli,Brown, et al., 2009)。然而, 过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他人的怜悯, 当怜悯指向自我之后, 它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最近, 有学者(Neff, 2003a,2003b)提出了自我怜悯(self-compassion)这一概念, 并对之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 自悯这一构念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应用中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文尝试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接下来, 文章首先对自悯进行了界定, 指出了引入自悯的必要性, 它的成分以及类型; 之后介绍了自悯在个体上分布出现差异的影响来源; 最后我们回顾了自悯的心理功能以及它在临床上的应用。
2 自悯的界定
2.1 自悯的来历
Neff (2003b)论称, 之所以需要提出另一构念来描述个体的自我观(self-view)其原因在于自尊并能反映个体心理健康和幸福的程度。因此在介绍自悯之前, 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尊与个体心理功能的关系。长久以来, 对于学术界和大众而言, 高自尊都是值得追求的, 因为高自尊即意味着高成就, 好人缘。但是, 最近的研究却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 综述见 Baumeister,Campbell, Krueger, & Vohs, 2003)。高自尊在带来心理益处的同时, 也往往会导致偏见, 攻击以及一系列自我保护或者自我抬升的策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矛盾, 一些学者认为高自尊具有异质性(Baumeister et al., 2003; 田录梅, 张向葵,2006)。高自尊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构念, 它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形式。例如, 研究者开始从自尊的稳定性(Kernis & Waschull, 1995), 自我价值的权变性(contingency of self-worth; Crocker &Wolfe, 2001)以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相异性(Bosson, Brown, Zeigler-Hill, & Swann, 2003;Jordan, Spencer, Zanna, Hoshino-Browne, &Correll, 2003)等方面来界定和厘清高自尊的不同形式, 即安全的(secure) 和易损的(fragile) 自尊(Kernis, 2003; Kernis, Lakey, & Heppner, 2008)。不过有学者也另辟蹊径, 他们提出了新的理论构念来替代自尊, 例如核心自我评价(coreself-evaluation) (Judge, Erez, Bono, and Thoresen,2002; Judge, 2009; 杜建政, 张翔, 赵燕, 2007)等。与后者的取向相一致, Neff (2003a, 2003b)提出了自悯。其中, 对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多集中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 与其说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不如说它是对既有概念的整合。最初, Judge 及其同事有感于自尊预测效度的微弱, 在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神经质等特质测量的基础上, 抽取了一个更广的构念, 即核心自我评价来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预测。而Neff (2003a, 2003b)对自悯的概念化更多地缘于自尊所带来的消极效应, 鉴于相关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其所预示的未来研究前景, 本文聚焦于对自悯的论述。
Neff (2003b)所提出的自悯构念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涉及自我观的问题。自我观指的是人们怎样看待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自我观常常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 自己的行为以及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表现得来(Swann, Chang-Schneider, &Mc-Clarty, 2007)。自我观可表现为自我概念、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多种形式。以自尊来描述自我观, 往往过于注重对自我的评判以及与他人的比较, 聚焦自我、超过他人又会导致对他人感受和需要的忽视, 从而加剧了与周围人的分离和孤立(Crocker & Park, 2004)。然而,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生物, 关联需要(need forrelatedness)是人类的根本需要之一。就如Bauer和Wayment (2008)在有关“清静我”(the quiet ego)(超越自我中心和自私)的文章中所论称, “他人是相对清静我的心理社会之和谐的一分子。”正如下文所述, 自悯不仅包含了自尊中所蕴含的对自我的接纳和肯定, 而且还把自我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 在自我观的问题上, 自悯代表了另一种新的自我观形式。
自悯的思想来源更多地汲取了佛学的思想,在佛学中的对应词更接近于“悲”。虽然出自佛学,但是对人类的幸福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参与对自悯的研究。事实上,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 东方的思想智慧愈来愈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关注(Houshmound, Harrington, Saron, & Davidson,2002)。例如, 有学者把佛教古老的修行术—— 正念(mindfulness; 如, Brown, Ryan, & Creswell,2007)引入了临床和健康心理学; 从佛教的视角来审视情绪心理学中的议题(Ekman, Davidson,Ricard, & Wallace, 2005); 来自中国儒家文化和诗学的“ 品味” 概念(savoring; Frijda &Sundararajan, 2007)也被运用于情绪心理学的研究等。所有这些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自悯就是当前这种趋势下的产物之一。下面将介绍自悯的成分和类型。
2.2 自悯的成分
在Neff (2003b)的理论分析中, 自悯指的是对自己的关心和关切, 与此同时自我聚焦(egoistic self-focus)又被最小化, 就如在引言中所提到的, 自悯包括了与对待他人相似的立场来对待自己的遭遇。它涉及“对自身的痛苦和困难保持开放性, 体验到对自己的友善和关切, 以理解的、非评判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足和失败, 并且认识到自己的遭遇是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因此, 她把自悯分成三个成分, 即自我友善(self-kindness), 普遍人性感(the sense of commonhumanity)和正念(mindfulness)。
自我友善指的是关心和理解自己的倾向, 而不是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在留意到自己人格中不好的方面时, 人们会“宽以待己”。即使当某些人格特征是有问题的且需要改正的时候, 人们也会无条件地接纳自我。在周围的生活环境非常艰难,让人心生痛苦时, 人们不会硬挺着; 相反, 自悯的个体会转向内部寻求自我宽解和安慰。
普遍人性感是自我怜悯的中心, 包含了对人无完人的承认, 即认识到所有的人都会失败, 犯错, 或者沉湎于不健康的行为。自我怜悯把自己有缺陷的状况和人类共有的状况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从更为宽广和囊括性的视角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遭遇。但是, 人们有时也会误认为只有自己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 而其他的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因而也会经受孤立感。
正念是自我怜悯的第三个成分, 它指以一种清晰和平衡的方式觉察到当前的情形, 既不忽视也不对自我或生活中的不利方面耿耿于怀(Brown, Ryan, & Creswell, 2007)。为了使怜悯扩展至自我, 个体必须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正念包含了某种对自己的超脱, 从元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经历, 因而能更现实客观地考虑自己的经历。与这种平衡的觉察状态不同, 人们有时会对所觉察到的负性体验表现出过度沉迷(overidentification)或者思虑(rumination)。一旦如此,个体就会愈加严厉地评判和指责自己, 并且体验到孤立和疏离感。
虽然自悯的这些方面在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却相互引起并相互促进。首先, 正念作为一种平衡的觉察状态, 为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提供了心理空间。它允许人们与负性体验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 从而保证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的生成。正念对其他的成分也有直接的作用。非评判的, 跳脱出来的正念减轻了自我批评, 增加了自我理解(Jopling, 2000), 从而直接增强了自我友善。同时, 平衡的正念也能克服自我中心,提高与他人的关联感。其次, 自我友善和关联感也能进一步地增加正念。例如, 如果个体停止评判和指责自己, 而代之以自我接受, 那么情绪体验的负性影响就能相应的减少, 从而更易于维持一种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平衡觉察(Fredrickson, 2001)。类似地, 如果意识到痛苦和个人失败是所有人都会遭遇的, 个体也会提高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正念觉察, 而又不至于过度沉迷。最后, 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也会互相增强。当自我受到严厉地批评时, 自我意识就会加强, 而这种自我感的提高又会增加孤立感。而友善地对待自己能弱化这种自我意识, 从而更多地为关联感留有空间。反过来, 意识到他人会和自己一样遭遇痛苦和个人失败也能减轻施加于自身的责备和评判(Neff, 2003b)。
总体而言, 我们认为自悯的三个成分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自我友善可以看作自悯的情感成分, 让个体无条件的接受自我; 普遍人性感可以看作自悯的认知成分, 它可以通过社会比较等过程扩展个体的视野; 而正念可以看作自悯的高级调节控制成分, 它可以把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调节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同时, 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对正念也存在一个反馈性的影响。相对于以自尊形式刻画的自我观, 自悯并不以外界结果而转移(自我友善); 不是寻求自我对他人的超越, 而是从自我与他人的共有要素中把自我与他人关联起来(普遍人性感); 更重要的是, 自悯还引入了正念, 即超脱的觉察(detachedawareness) (Bauer & Wayment, 2008), 正是这种觉察保证了对此时此地中自我和他人解释的更少防御性。
2.3 自悯的研究方法
为了从实证上对自悯进行研究, Neff (2003a)依照自悯的三个成分编制了自悯量表。它由26个项目构成, 这些项目又分属于6 个子量表:自我友善, 自我评判, 普遍人性, 孤立感, 正念和过度沉迷。子量表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子量表之间的相关可由一个二阶的因子解释, 即自悯。自悯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 即较高的重测信度(r = 0.93)和内部一致性信度(α = 0.92), 聚合效度和辨别效度, 如自我报告的自我怜悯量表分数与观察者的报告有很大的重合, 佛教徒比非佛教徒报告了更高的分值(Neff, 2003a; Neff, Kirkpatrick, & Rude,2007)。从量表的内容可以看出, 它主要是对特质性的自悯进行测量。
除了使用量表对特质自悯进行测量之外, 也有研究者采用诱发的方法使被试产生状态自悯(Leary, Tate, Adams, Allen, & Hancock, 2007)。在他们的研究中, 对应于自悯的三个成分, 首先,让被试罗列出他人也会同样经历类似的负性事件(普遍人性感); 然后, 让被试书写一段文字,内容涉及以对待经历负性事件的朋友的方式, 对自己也表达出理解、友善和关切(自我友善); 最后, 让被试以客观冷静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对负性事件的反应(正念)。研究结果发现, 状态自悯能够被成功地诱发出来, 自我怜悯组的被试在回忆负性事件后报告了更少的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他们也更有可能对事件承担个人责任(Leary et al.,2007)。
除了应用自我报告这种主观的测量方法之外, 还有一些客观测量方法可以应用, 例如:行第18 卷第12 期 自我观的新形式:有关自悯的研究论述 -1875-为测量、生理测量等。外显行为的测量主要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方面的测量。生理测量不仅包括包括心跳、血压、皮肤电等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 还包括脑机制的测量。尽管这些方法还没有在自悯研究领域得到应用,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测量、生理测量的方法也会成为测量自悯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自悯的影响因素
自悯作为一种自我观, 无论在特质水平上还是在状态水平上都存在着个体差异。究竟个体在自悯上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能够清楚地确认自悯的影响来源, 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 提高个体的自悯心, 进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Neff 和McGehee (in press)对青少年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母亲的批评和紧张的家庭关系与自我怜悯呈负相关。而那些体验到来自父母接纳和肯定的个体则报告了更高的自我怜悯。安全的依恋与自我怜悯呈正相关, 而先占和恐惧依恋与自我怜悯呈负相关, 从而表明了依恋在自我怜悯中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Gilbert(2005)从进化的角度指出, 自我怜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依恋系统, 所以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或者经历过与照料者之间支持性和肯定性关系的个体更有可能以关心和同情的方式看待自己。相反, 那些在不安全甚至威胁性的环境中得到抚养或者经受不断批评和攻击的个体往往会自我批评而不是自我怜悯(Gilbert &Proctor, 2006)。
Neff 等人(Neff, Pisitsungkagarn, & Hseih,2008)也检验了自悯跨文化的普遍性。他们选取了泰国、美国和我国台湾的被试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自悯、独立型和互倚型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心理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自我怜悯的平均水平在泰国最高, 我国台湾最低, 美国处在中间。Neff 等(Neff et al.,2008)认为这种跨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泰国人受到佛教强有力地影响, 人们在日常交往和教养中会强调怜悯的价值; 而我国台湾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 羞耻心和自我批评被作为一种家长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得到强调。美国之所以报告了中等水平的自我怜悯是因为美国文化对自我怜悯显示了更加复杂态度(强调积极自我情感却又包含孤立和竞争的民族精神)。不过在这三个文化中, 更高程度的自我怜悯都显著地预测了更少的抑郁和更大的生活满意度, 从而表明了不管文化的差异如何, 自我怜悯的益处是普遍的。
从既有的研究可知, 自悯作为一种个体的特质, 不可避免会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 小到早期的成长经历, 大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然而,心理系统不仅对外部的环境作出反应, 系统之间也会发生相互的影响, 例如, 在一项有关自我怜悯和主要人格特质关系的研究中(Neff, Rude etal., 2007), 研究者发现自我怜悯与神经质有最强的相关(r = −0.65), 自我怜悯同样与宜人性、外倾性、尽责性有正相关, 但是却没有发现其与对经验的开放性有关系。探讨自悯与其他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从不同的角度对自悯进行考察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人类的自悯系统对自身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对适应社会是否有帮助?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下文将就这一议题展开论述。
4 自悯的功能
自悯作为自我观的一种表现, 对个体的心理功能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与自尊不同的是,它似乎并没有产生连带的副作用。下面将主要介绍自悯在个体应对负性事件上的缓冲抵御功能,它与积极心理力量的关系以及自悯在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功能。
4.1 自悯的应对功能
根据Neff (2003a, 2003b)的理论阐释, 高自悯个体对自身的问题、缺点和不足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但是他们不是严厉地批评和指责自己, 而是代之以关切和怜悯。因而, 自悯能够帮助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件, 缓冲它们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 自悯又能培养起积极的自我感。因而, 高自悯个体往往具有高自尊。但是, 自悯却不同于自尊, 自尊往往导致个体自大、自恋或者自我抬升的错觉, 而自悯却不会。Neff 和Vonk (2009)的研究发现, 自尊与自恋有显著的正相关, 而在控制了自尊水平之后, 自我怜悯与自恋则不存在关系。在控制了特质性自尊之后, 低自悯仍解释了个体在抑郁和焦虑上相当大的变异(Neff,Hseih, & Dejitthirat, 2005)。
为了更细致地检验自悯与焦虑之间的关系,Neff, Kirkpatrick 和Rude (2007)进行了实验研究。-1876-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他们首先创设了模拟面试场景, 参加实验的被试需要以书面的形式写出自身最大的缺点。研究者除了测量自悯之外, 还施测了积极和消极情感、自尊以及状态焦虑。研究结果发现, 在考虑了自身最大的缺点之后, 自悯与焦虑呈负相关。即使控制了情绪诱发前的负性情感水平和自尊后, 偏相关依然显著。后继的文本分析显示, 低自悯者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而高自悯者更可能使用第一人称复数, 从而表明自悯包含了从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看待自我。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自悯与负性情绪词的使用无关, 从而支持了研究者的猜想, 即自悯并不是通过回避负性情感的体验来减少焦虑的。在另一项运用体验取样法的研究中, Leary 等(研究1, Leary et al., 2007)考察了日常生活中, 自悯对负性事件的缓冲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高自悯个体在遇到糟糕的事情后更倾向于友善地对待自己, 使自己感觉尽快好起来, 从多个角度审视他们的状况。Leary 等(研究3, Leary etal., 2007)接下来继续探讨了在面对消极反馈后,自悯对个体的认知效应。例如, 无论是收到中性反馈还是积极反馈, 高自悯者都会适度地把反馈归因为自身的人格; 而低自悯者似乎更多地做出了防御性的归因, 相比于中性的反馈, 他们更有可能把积极的反馈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反映。在Leary 等另一个的研究(研究4, Leary et al., 2007)中, 被试首先面对镜头虚构一个故事, 然后让包括自己在内的三组被试充当评价者, 即自我评价组、高自悯评价组以及低自悯评价者。结果显示,低自悯者往往会给予自己更为消极的评价, 而高自悯者对自己的评价则和观察者的评价相一致。从而说明, 高自悯者对自己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高自悯个体在遭遇到失败或者挫折时会更多的运用情绪聚焦应对中的接纳、积极再解释和成长等策略, 更少的采用回避策略(Neff et al.,2005)。最近, Adams 和Leary (2007)考察了自悯对节食者的影响。先前的研究发现, 对于高自我克制的饮食者而言, 一旦破坏了自己的节食计划,他们往往会在随后的饮食中吃的更多。Heatherton和Polivy (1990)认为这种贪食模式的目的在于减少与违背节食目标相关的负性情感。但是自悯状态的诱发却能降低这种效应, 研究中的节食者在诱发出了自悯之后体验到了更少的负性情绪, 她们也吃了更少量的甜点。
自悯所提供的心理弹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 Neff (2003a)的研究显示自悯个体往往更少地卷入思虑(rumination)和思维抑制(thoughtsuppression)。从概念上来说, 高自悯者会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情绪体验, 所以个体既不会逃避这些情绪也不会沉湎于这些情绪, 也就是说自悯心强的个体更能直面个人的缺点和生活中的困难。
4.2 自悯与心理力量
自悯不仅可以提供个人免受负性事件困扰的防护衣, 它还可以增强个体积极的心理力量。自我怜悯与幸福和乐观这两个心理健康的重要特征存在很强的联系。相比于社会支持, 自悯甚至预测了更大比例的幸福感(Neely, Schallert,Mohammed, Roberts, & Chen, 2009)。另外, 自悯还与个人主动性、积极情感、好奇和探索性以及反省智慧和情感智慧呈正相关(Neff, Rude, &Kirkpatrick, 2007)。这些心理品质正是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积极心理力量(Seligman &Csikzentmihalyi, 2000)。更重要的是, 自悯还与自主感、胜任感以及关联感有关(Neff, 2003a), 这表明自我怜悯有助于满足个体基本的需要。Deci 和Ryan (2000)主张这些基本的需要是人类幸福的根本。如前所述, 自我怜悯并不仅仅是积极思维的一种形式。自我怜悯指的是在非评判性的觉察中对负性情绪的容纳能力, 而不是压抑或者否认自我体验的负性方面。例如, 自我怜悯的个体在描述自己的缺点时, 并没有使用更少的负性情绪词, 他们只是在考虑这些弱点时更少的焦虑而已(Neff, Kirkpatrick, & Rude, 2007)。
自悯的心理功能还表现在它能超出情绪应对的范畴, 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发挥作用。例如, Neff 等人(Neff et al., 2005)发现, 自悯与个体的所采取的学业成就目标有显著的相关。具体来说, 自悯与掌握目标正相关, 而与表现目标负相关。这些关系以更少的失败恐惧、更大的胜任感为中介。此外, 自悯还与个体的内部动机有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 高自我怜悯的个体具有更强的学习和成长动机, 但是这些动机只源于内部原因, 而不是为了外部的奖励和强化。Magnus 等人(Magnus, Kowalski, & McHugh, in press)的研究显示, 高自悯女性对运动的参与主要受到内部动机的驱动, 更少体验到来自社会有关体型的焦虑,第18 卷第12 期 自我观的新形式:有关自悯的研究论述 -1877-因而在运动中并没有强迫感。此外, 高自悯个体也报告了更少的拖沓倾向(Williams, Stark, Foster,2008)。
4.3 自悯的社会功能
自悯作为一种特质, 不仅能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际知觉和社会互动。例如, Leary 等(研究4, Leary et al., 2007)的研究发现, 在对他人的表现评价上, 高自悯观察者和低自悯观察者则是一致的。这似乎表明观察者自悯程度的高低与对他人的评价无关, 高自悯者并没有给他人更为积极的评价。虽然如此, 和低自悯者相比, 高自悯个体却在接受到中性的反馈后对评价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喜欢程度(研究3, Leary et al., 2007)。此外, 被评价者的自悯程度可以预测评价者的负性情绪, 评价者在观看到低自悯者的表现后, 体验到了更大的负性情绪, 这或许是因为, 低自悯的被评价者把自己的不自在暗中传递给了评价者(研究4, Leary et al., 2007)。虽然在评价他人的表现上没有出现差异, Neff (见Neff, 2009)却发现,高水平自我怜悯的个体报告了更大的宽恕他人的倾向, 他们更有可能采择他人的观点, 在考虑到他人的不幸时会更少地感到个人痛楚(personaldistress)。尽管如此, 自悯与对他人的共情(有关共情的综述见 刘聪慧, 王永梅, 俞国良, 王拥军,2009)和利他主义倾向并没有显著的相关。
从上面的介绍中, 我们不难看出自悯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心理功能。但是回顾既有的研究也不难发现, 大多数的研究都停留在相关水平(方法大多为问卷法), 很难在现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因果推论。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实验的方法考察自悯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贡献。
5 自悯的临床应用
有关自悯的概念和实证研究都表明, 自悯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鉴于此, 临床方面旨在培养自悯的治疗项目也得到了开发和应用, 已有研究表明有些干预治疗效果显著。Neff及其同事(Neff, Kirkpatrick, & Rudes, 2007)进行了一项为期一个月的“自悯体验变化”的研究。治疗师使用了格式塔双椅技术(gestalt two chair,Greenberg, 1983)来减缓当事人的自我批评, 增强对自己的怜悯。在实施过程中, 自我的两个相互冲突的方面会表达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是自我批评的声音, 另一个是受到批评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得以充分表达各自的价值、需要。治疗师首先让来访者设想一种自我批评的情境; 接下来,来访者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确认另一种声音来对自我批评作出反应; 最后, 在这两种声音之间进行一场对话, 并在两个椅子之间轮转。一旦这种冲突确立之后, 治疗师就开始训导来访者, 保证两种声音注意和倾听了彼此的真实感受。当治疗师认为冲突已经解决, 对话即告结束。训练的目标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让自我重新认识和发现自己的价值。结果显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随着自悯水平的增加, 个体体验到了更少的自我批评、抑郁、思维抑制和焦虑。
Gilbert 和Procter (2006) 最近开发了一种基于团体的治疗干预措施, 即所谓的“怜悯心理训练”(compassionate mind training, CMT)。此项目以社会心理理论(Gilbert, 2005)为基础, 用来协助人们形成自我怜悯的技能。CMT 假定, 某些人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时并没有形成理解痛楚来源以及自我抚慰的能力, 他们往往会自我抨击。因此,治疗的目标在于当人们在体验到威胁或者自我批评时, 教会他们如何自我抚慰以及产生怜悯和温暖的感受, 并最终在自我与自我的关联中激活抚育给予心理(care-giving mentality)。它要求患者设想或者回忆自己对待他人的怜悯动机或者情感, 从而有助于个体把这种指向外部的怜悯情感转向自身。此外, 它还要求患者想象理想的自我关切。CMT 的结果显示, 训练后被试在抑郁、自我攻击、自卑感、服从行为和羞耻等水平有显著的降低。
另外的干预措施还包括Kabat-Zinn (1982)所形成的基于正念的应激化解策略(mindfulnessbasedstress reduction, MBSR)。这个项目旨在培养参与者对当前思想、情感和身体感觉的非评判性的觉察。由于练习者习得了如何让有关过去的思虑和对于未来的恐惧消散, 他们会产生更大的“此时此地”的觉察性状态, 进而他们能看到自己对待压力的习惯性反应, 培养起更为健康和适应性的反应方式。干预措施包括了冥想(meditation)、身体扫描、瑜伽等。虽然这个项目不是有针对性地增加参与者的自悯, 但是干预的结果却显示, 练习者的自悯程度升高了, 而应激-1878-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水平却下降了(Shapiro, Astin, Bishop, & Cordov,2005; Shapiro, Brown, & Biegel, 2007)。
尽管各研究者和治疗师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法和手段, 但是治疗的效果都显示个体的自悯程度增加了。虽然自悯作为一种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自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敏感, 在和环境的交互中比较容易改变, 当人们对生活中的难题感到无力应对时, 提高自悯能有效增强人们适应环境的水平, 从而缓冲消极事件的影响。
6 小结与展望
自悯在有关自我的研究中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 自从Neff (2003a, 2003b)首次提出到现在也只有六、七年的时间, 但是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 自悯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免受挫折、失败等让人痛苦的负性事件的影响, 而且它还可以增强人们的积极心理品质, 推动个体追求自身潜力的实现。由此可见, 自悯对个体心理健康和幸福的积极影响是有效而广泛的。然而, 自悯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 尚有很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查。以下是我们对自悯相关研究领域的几点展望。
第一, 鉴于以往研究在支持自悯缓冲器作用方面一致和普遍的发现, 有必要把自悯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从上文的回顾中可知, 对自悯积极效应的检验大多集中于个体事件上, 当面对群体水平的负性评价时, 自悯是否还能帮助个体化解消极影响就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例如, 研究者可以考察自悯在人们应对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相关综述见, 阮小林, 张庆林,杜秀敏, 崔茜, 2009)等情境时的效力。
第二, 与自悯在个体内(intrapersonal)显著的积极功能不同, 有关自悯在个体间(interpersonal)功能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却存有分歧。例如,高自悯个体能更多地考虑到他人的观点, 报告了更多的宽恕他人的倾向, 但是, 高自悯者对他人的表现并没有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 自悯与对他人的共情和利他主义倾向也没有关系。Gilbert(2005)论称, 自悯与个人早期的依恋系统关系密切, 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可能知觉到他人的痛苦, 并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出怜悯的反应(Mikulincer & Shaver, 2005)。这在理论和实证上似乎是相矛盾的。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那么反过来是否也会成立?自悯与悯人是否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探索。
第三, 自悯与邻近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梳理。近年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研究者加大了对积极心理属性的探讨。一些重要的心理品质受到了研究者的重新重视。例如, 如实性(authenticity)就得到了积极心理学的推崇(Linley,Joseph, Harrington, & Wood, 2006)。最近有研究者(Wood, Linley, Maltby, Baliousis, & Joseph, 2008)对如实性从理论上进行了概念化, 他们强调意识觉察和真实体验之间的匹配性( 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意识觉察与行为之间的相容性(如实生活, authentic living)、承认他人影响(接受外部影响, accepting external influence)为如实性的三个方面。从他们的概念界定中, 我们不难看出如实性和自悯之间的相似处, 它们都强调对真实体验的觉察和接纳。因此, 该怎样对自悯和其他近似的概念进行整合也是研究者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四, 作为对自尊的补充, Neff 提出了自悯的概念。最近, 有研究者(Martens, Greenberg, &Allen, 2008)论证了状态自尊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 他们指出副交感神经中的迷走神经与自尊密切相关。与自尊的应对功能相似, 自悯能有效地帮助个体应对负性的生活事件, 然而这种效应的神经生理机制尚有待确认。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似乎提供了一些依据。例如, 对冥想或正念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显示, 短时间的悲悯冥想(compassion meditation)能显著地影响与应激相关的脑区, 如前扣带回和海马(Lutz, Slagter,Dunne, Davidson, 2008); 悲悯冥想也影响到了个体对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先天免疫和行为方面的反应(Pace et al., 2009)。不过, 是否存在特异于自悯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最后, 虽然最初Neff 在概念化自悯时从自尊的不足入手, 但是正如文中所述, 在控制了自尊后, 自悯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反之亦然; 自尊和自悯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这说明自尊和自悯是两个不同的构念, 然而它们又存在着共同的部分。它们或许都是自我观的一种形式而已。在不同的情境和状况下, 它们或许协同起作用, 又或者对立起来。探索自悯和自尊各自发挥作用的条第18 卷第12 期 自我观的新形式:有关自悯的研究论述 -1879-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是未来的一个研究议题。
总之, 对自悯心的研究虽然刚刚起步, 然而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却显而易见, 与自悯有关的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